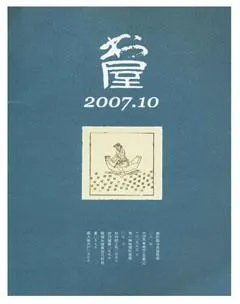高教收費政策不宜大動
一、選擇的艱難
較長時間以來,社會各界對高校擴招和收費政策頗多微詞,可謂眾說紛紜,反對之聲不絕于耳。現在,已到評估這項公共政策的時候了。
首先,我并不同意“教育產業化”(以商業經營為價值指導)的總體定位,不同意將公益性很強的教育辦成惟利是求的商業性操作模式。但是,我們必須面對嚴峻的現實國情:人多底薄經濟太差、教育整體水平太弱,資金缺口巨大。“希望工程”歷時二十年,所募助教善款僅二十億(只夠修三公里地鐵)。因此,中國教育的發展只能筑基于社會經濟的整體發展,沒有經濟的實質支撐,僅靠道德的呼喊,無論如何是空洞乏力的。
要求政府拿出辦教育的所有經費,視教育為慈善,這一思路仍走在“萬能政府”的老路上,以為政府能夠解決一切,能夠包辦一切。教育確實不能產業化,但也無法慈善化,尤其高等教育,不可能再搞上世紀五十至七十年代的包辦制。實事求是地說,接受高等教育畢竟是個人追求發展的一種需要。在普遍貧弱的現實國情下,要求完全由政府或社會承擔高等教育費用,是不現實的。而且,政府或社會從哪來錢?當然,政府應該削減政費軍費、削減基建投資、增大教育投入。這些年,政府投入較低確為事實,2005年教育總支出不足四千億,僅占GDP總額百分之二點一六,低于2004年百分之二點七九與2002年的百分之三點四一。世界各國均值百分之五點二,高收入國家在百分之五點五以上,低收入國家平均也達百分之三點六,中國人均財政教育經費僅相當于發展中國家平均水平的四分之一,被聯合國教科文組織列為世界倒數第八位〔1〕。但是,政府再加大投入、再怎么從其他地方挪補也是有限度的,較之教育經費之大缺口,也是一下子填不滿的,這是必須承認的事實,即現實國情。
就是中小學初級教育,1990年代的十年間,全國對農民征收的“教育附加費”和各種“教育集資”,最保守的估計也在一千五百億元。沒了這一筆錢,連中小學教育都撐不下來的。原國家教委副主任柳斌說:“2006年以前,我們的義務教育沒有成為公共財政保障的教育,財政只保障一半,有一半要靠社會籌措。”〔2〕
就是相對富裕的東部沿海地區,各地政府仍無力承擔教育所需全部資金,托舉不起這只大盤。相對富裕省、縣能夠保證轄境內九年義務制教育所需經費,已經阿彌陀佛了。吃飯生存、發展經濟、醫療保健、教育投資……誰都重要,誰都要錢,誰都得帶著拽著,款額又只有這一點,蛋糕本身就小,不考慮現實平衡是不可能的,也是不負責任的。必須承認,任何選擇都不可避免地會受到來自理想與現實的雙重掣肘,任何稍有偏重的選擇都會遭到其他方面的譴責,都會聽到“應該這樣”、“應該那樣”的各種訴求,而不同時期有所偏重又是無法避免的。
更重要的是:由于經濟基礎薄弱,我國用于教育的公共開支尚不足世界教育開支總量的百分之三。再據1990年代末統計,我國各類在校生為二億八千三百一十六萬,約占世界受教育人口總數的四分之一。2006年3月3日,教育部長周濟在人大會議期間記者招待會上說:解決了百分之九十五學齡人口的義務教育。必須承認:我們是在以極其微弱的財力承辦全球規模最大的教育,其中艱難可想而知。研究者指出:“這一基本國情決定了我們必須有效地使用公共教育開支,同時必須鼓勵增加私人和社會的教育投資。國家沒有必要也不可能對所有的教育和受教育人口大包大攬。”而且根據發展中國家教育投資的社會收益率,小學教育為百分之二十七,初高中為百分之十六,大學為百分之十三,因此“作為人口眾多的最大發展中國家,我國政府必須全額資助小學教育和初中教育,大學教育理應增加私人投資。”〔2〕再以小學與高校3f2f40ae99a42d8ad52ee26f52675941a1e9fd57f67246b6e7d344a272f1f8fb生均經費投入來看,1998年小學生人均經費三百七十點七九元,高校生人均經費則為六千七百七十五點一九元,相差十八點三倍。此前差距還要大〔3〕。再說大學生,上海財大生人均經費一萬五千元/年,北大生人均經費兩萬五千元/年,學生所繳納每年五千元學費,只是負擔了三分之一至五分之一〔5〕。顯然,以國家目前財力,實在無法包辦高等教育。按目前執行的《高等學校收費管理暫行辦法》第五條:“在現階段,高等學校學費占年生均教育培養成本的比例最高不得超過百分之二十五”,正規院校(尤其重點高校)大致控制在這一比例之內。
還有一則資料。清華、上海交大、浙大,1991年總經費僅為一至一點五億元,而同期美國康乃爾大學六點八六億美元,麻省理工十四點零二億美元,伯克利加州大學七點七億美元。世界一流大學的經費是我國名牌大學的六十倍之巨。僅僅一所麻省理工所擁有的經費就是我國1991年三十六所委屬高校總經費的六倍〔6〕。
據最新資料,目前全國教育部屬七十二所院校總負債三百六十億元,平均每所部屬院校負債五億。之所以欠債如此之高,原因即在于高校招生規模急遽擴大,從十年前招生不足百萬發展到目前五百萬/年。全國大學也從十年前的一千所左右發展到今天的兩千所〔7〕。
眾所周知,任何政策都不可能十全十美,不可能沒有一點負面效應,尤其在“沒錢也要辦事”(或錢少也要辦事)的中國,任何政策選擇都是十分艱難的。關鍵在于利弊相權之下的理性權重與科學把握,在于各種因素之間盡可能的精準調配。優先發展高教的思路,既因較之中教小教,高教總盤子最小,所需資金絕對數最少,更為關鍵的是對全社會的價值導向。如果教育界龍頭老大高校教師的收入持平于中小學教員,那么知識的優越性便無從體現,社會成員自覺追求知識化就會失去現實激勵。畢竟,高校教師所需知識積累量要大大超出中小學教師。
二、高教收費的可行性
2006年3月4日,北大張維迎教授在某一內部研討會上說:“我過去講過一句話,也是挨罵最多一句——為什么窮人上不起大學,因為學費太低。什么意思?世行研究,歐洲也研究,我們用低學費的辦法都是補貼,但不是補給窮人。我們如果規定學費多少用于窮人助學金,這一問題就可以很好的解決。不要按計劃經濟統一的標準,就像病人,有錢人和沒有錢的人看一個醫生,這樣是走不通的。”張維迎的意思是用高收費之策進行貧富調節,使學校補貼真正的貧困生,而不是通過降低學費這一普惠制使非貧困生均沾利益,致使學校失去補助貧困生的能力。降低學費,學校失去財政能力,不僅無助于救助貧困生,而且教學質量必然下降——優秀師資外流。
據統計,全國高校生均學費1989年為兩百元左右,1995年八百元左右,近年四千至五千元左右,十八年間確實上漲了二十至二十五倍〔8〕。同期職工工資從兩百元以下漲至二千至三千元左右,當然職級、行業、地區之間的差距很大,但十八年間全國職工收入增幅至少在十五倍左右,農民平均收入達不到十五倍。從這一角度,學費漲幅高于收入漲幅,存在相對的不合理性。但這一傾斜性收費政策,即通過高中、高校收費,引導國民收入匯聚教育,從整體上支持教育發展,真正體現了教育優先的發展思路。
中國高校為什么不能合理吸納社會資金?為什么不能執行“誰得益誰支付”的原則?更重要的是:如果以慈善性代替價值規律,便會打破目前好不容易建立起來的價值理念與現實平衡,便會重見那一系列熟悉之至的計劃經濟時代的舊弊舊癥。至于城鄉貧困家庭子弟無力繳納學費,則可通過各種補助性質的“綠色通道”予以解決,總不能在收費政策比照“缺口效應”——以最低收入者為基準。因為少數貧困家庭無力納費,便從整體上否定收費政策或指責收費過高,實際上是破壞整體平衡,否定“教育優先”。所謂“優先”,其實質就在于必須保證經費優先。
以上海高校為例(上海生活費用較高,貧困劃定標準高于全國平均線),家庭收入人均每月四百元以下為貧困生,三百元以下為特困生。上海各高校貧困生(包括特困生)約占全體在校生的百分之二十,上海財經大學近年為百分之十三,其中百分之五左右為特困生,這里面必然有一部分“虛貧生”(故意裝窮者,學校不可能徹底一一核實)。可見,貧困生總體比例并不高,遠未達到需要考慮停收高校學費的地步。如果為了這些貧困生,改變收費這一大政策,那么中國高校財政不是斷了一條重要輸血管,一條能夠得到百分之八十以上大學生家庭支持的輸血管?有數據表明,近年全國高校經費來自國家財政投入已不足百分之五十〔9〕。某高校計財處長說:“如果嚴格按《高等學校收費管理暫行辦法》第五條收取學費,學校就得關門。”〔10〕
必須承認,確有下崗工人或貧困農民因湊不齊子女的高校學費,走了極端跳了樓;也有中西部一些貧困縣農民十年不吃不喝供不起一名大學生。但這些個別案例并不能證明高校收費的殘酷性,并不能撼動收費政策的整體合理性。就像有人忍受不了競爭壓力而自殺,難道就能從整體上推翻競爭體制么?別忘了,僅僅依靠道德是無法推動社會這架大轉輪的。
中國之大,各地發展之不平衡,任何一項全局性政策都需要一定的補缺,但局部的補缺并不等于整體的全部推翻。適當運用市場機制,盡量調動一切社會力量興教辦學,再以其他補救性政策遏制負效應,應該說是相對合理的政策。目前高校對貧困生采取“綠色通道”——先入學后商量解決費用(減免學費、貸學金、助學金、獎學金等等),即“獎貸助補減”五種救助性措施,沒錢也能上大學。據報道,2006年國家助學貸款已資助二百四十點三萬貧困生讀大學,2005年有三十九萬貧困新生通過“綠色通道”未交學費直接入學〔11〕。陜西省累計八萬五千名貧困生得到國家助學貸款五億九千萬元;其中四點五萬貧困生所得三點一億貸款,得自2004年6月實施國家助學貸款新機制以后〔12〕。
還有一點需要指出,貸學金政策執行六年來,除京滬等大城市畢業生還貸率較高(因收入較高),中西部地區還貸率極低,河南全省至2005年只有一名畢業的貧困生還清貸款〔13〕。全國有百分之二十的借貸生逾期未還〔14〕。2006年9月,陜西省教育廳下發通知,要求加強對貸款學生的誠信教育,對違約一年以上不還貸的學生將在媒體及網站公布其姓名與相關信息〔15〕。就是上海,2006年9月,農業銀行將九十六名助學貸款不還者告上楊浦區法院,這些已畢業的貧困生如今每月僅需還款一百六十一元,仍然一躲了事。農業銀行此類欠款糾紛達三四千件〔16〕。不消說,所有未歸還的貸學金還是國家與高校共同買單,高校每年須向教育部協貸中心繳納本校貧困貸學金總額的百分之四點一為風險金,國家財政部也向該中心繳納百分之四點一風險金,共同作為銀行“壞貸”的賠償金,等于國家與高校為貧困生的高等教育作出“實際支付”。2001年國家財政高校特困生各類資金總額近七千萬(含助學貸款)〔17〕。教育部2006年3月8日發布消息,迄今共發放貸學金一百七十二點七億元,資助了一萬八千二百零六名貧困生〔18〕。由于“壞貸”總額遠遠高于風險金,銀行已有拒絕發放貸學金的動議,并要求對還貸還制定強制性措施。
就是歐美各國,教育投資也是家庭最主要的開支項目。如筆者姨妹夫婦(均為美國博士),家庭年收入十余萬美元,也承擔不起孩子入學哈佛、普林斯頓等收費很高的名校,只能讓孩子進入居住地的華盛頓州立大學,因為該州子弟僅收學費五千美元/年。
三、高教擴招的必要性
現在以大學生就業困難反對高校擴招論調不時泛起。實際上,所謂大學生就業難也只是相對于京津滬穗深等高收入城市職崗,若放眼全國,挺進中西部,進入中等城市或再深入縣鄉鎮,就業需求可是“大大的”。再以實際數據來看,2004年底,當年大學生就業率達百分之八十四,全國僅四十五萬多畢業生未于畢業后立即找到工作〔19〕。這一“未就業率”顯然不足以說明擴招過度。而且,“畢業即失業”乃普遍現實,哪個國家都不可能使本國大學畢業生百分之百充分就業,更不用說“滿意就業”了。如果大學畢業生一出現就業難,即以削減招生數相平衡,是一種能夠選擇的政策么?也許我們不得不承認現實的殘酷:一定程度存在的失業率,乃是促進人們珍惜工作機會的最大動力。
一頭是國家經濟發展需要高素質人才與社會進化需要成員素質提高,呼喚高校擴招;一頭是國民希望通過接受高等教育,提高自身競爭力、提升生活質量。可見,高校擴招乃是上下兩頭都呼喚都支持的現實需求,于國有益,于民有利。就是中國的政治民主化,也不僅僅是社會成員單向的享權,民主也對社會成員提出相應的文化要求。僅憑就業相對困難即否定擴招,是不是太片面了?至于將高校擴招歸之“延緩就業壓力”、“擴大內需”、“以教斂財”,亦均似是而非,責之失當。“延緩就業壓力”原本無錯,難道不需要延緩嗎?擴招既延緩壓力,又提高青年文化素質,難道不對嗎不好嗎?“擴大內需”、“以教斂財”(就算是),引導國民向他們愿意且正確的方向投資,錯了嗎?
據美國學者羅伯特·福格爾(諾貝爾經濟獎得主、芝加哥工商管理學院教授)1990年代末調研:中國人均實際收入與美國相差約一百年,但中學教育已達到1970年代水平,而當時美國人的人均收入為中國當時水平的十倍〔20〕。可見,以我們目前相對落后的人均收入支撐當前的中高等教育,確實體現了“教育優先”的發展思路。
不過,高校擴招確實也帶來一系列問題,需要慎重對待,如學生人均教學行政用房面積從十四點四平米降至十一點八平米,生均教學儀器值從六千四百零九元降至六千二百零九元,生均藏書從一百一十七冊降至六十一冊〔21〕。高校債務問題也越來越突出,有的大學已經虧損運行,連債務利息都無力償還〔22〕。研究者已經提醒若繼續擴大高校規模,國家經濟實力將難以支撐,呼吁我國高教發展重心應從增量轉向增質。但這些較之擴招所帶來的正面效應,顯為次要方面的負效應,可通過適當調節加以解決。如果因了這些次要方面的負效應,否定擴招的整體積極效應,實屬以偏概全,極為失當。再說,任何發展身后都不可能沒有一點最初的陰影,只要還在可糾可補的范圍內,就不應該因了這塊陰影否定已經邁出的腳步。
就中國教育現狀來說,雖然問題很多,需要不斷修正改進與加大投入,但基本政策還是對路的,或者說相對合于實際國情。至少,高校收費政策目前不宜大動。
注釋:
〔1〕〔5〕載《新華每日電訊》2006年3月8日第8版“兩會特刊”。
〔2〕載《南方周末》2006年10月12日A3版。
〔3〕載《內部參閱》1999年第4期((總第447期)。
〔4〕載《內部參閱》2002年第21期(總616期),2002年6月7日,第66頁。
〔6〕林樟杰:《論新時期中國的知識分子問題》,上海交通大學出版社1999年第1版,第176頁。
〔7〕〔8〕載《解放日報》2007年3月11日第3版。
〔9〕載《社會科學報》2006年3月9日第3版。
〔10〕《新華每日電訊》2006年12月31日第3版“新聞觀察”。
〔11〕載《半月談》2006年第8期。
〔12〕〔15〕載《新華每日電訊》2006年9月4日第2版“國內新聞”。
〔13〕載2005年12月23日《中國青年報》。
〔14〕〔18〕據央視12套法治頻道“中國法治報道”欄目報道,2006年3月10日12:00-12:30。
〔16〕載2006年10月9日《民主與法制時報》。
〔17〕載《內部參閱》2003年第4期(總第648期)。
〔19〕〔21〕載《社會科學報》2005年12月8日第5版。
〔20〕載《內部參閱》1999年第42期(總485期)。
〔22〕載2005年12月26日《光明日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