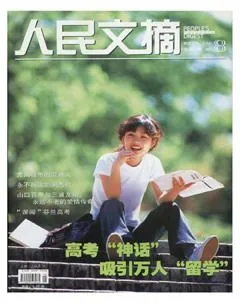多少往事付紅塵

上官云珠,這是一個曾經在中國電影史上熠熠生輝的名字。她塑造的許多角色,已經成為銘刻在一代中國人心中永恒的經典。但誰又知道,在這些令人炫目的光環背后,卻是一段段說不盡的辛酸滄桑往事。
低調平和的韋然,正式的身份是中國建筑工業出版社的編輯,負責上海地區的業務,卻又經常被熟悉的電影界長輩介紹,參加電影圈的諸多紀念活動。回憶起美麗的母親,那些經常讓韋然紅了眼圈的往事,已濾去了最初的巨痛,轉而成為一種淡然而持久的憂傷。
母親之死
1968年12月的一天,我突然接到姐姐的來信,讓我馬上回上海一趟。那一年,我只有17歲,剛離開北京到山西農村插隊還不到一個月。我心神不安地上了火車,不知道已經支離破碎的家,又出了什么事。
一路顛簸到上海,迎接我的是這樣一個噩耗:11月22日凌晨,母親跳樓自殺。
1966年,正在江西農村參加“四清”的母親得了乳腺癌,回上海做切除手術。手術很成功,她身體恢復得也很快。此時《舞臺姐妹》已被定性為“美化30年代文藝黑線的反面教材”而遭重點批判,母親與導演謝晉,電影女主角竺春花的原型——袁雪芬等被牽連。所幸那時有醫生的干預,她才被留在醫院,沒有過早被卷進那場險惡的政治浪潮。
但是兩個月后,母親又突然昏倒,檢查結果表明,病變組織轉移到了大腦。接下來她又做了一個大手術,從十幾小時的昏迷狀態下蘇醒過來后,幾乎不認得任何人。直到一個月后,母親給我寫了第一封信,告訴我她已經認得300個字了。
而此時,外面的形勢變得更險惡,她參演的《舞臺姐妹》與《早春二月》成了文藝界的兩株“大毒草”,母親一瘸一拐被趕出醫院。
此后的兩年,對母親來說是黑色的歲月。她出院不久就被逼去電影廠上班,所謂“上班”,其實就是每天去“牛棚”報到,那時她的身體,還遠未恢復到健康狀態。
50年代初,母親與其他文藝界人士曾被毛澤東數次接見,這一度保護她免遭“右派”的命運,但“文革”一來,這卻又成了她最大的罪狀之一。出事前一天,母親又一次被傳喚,兩個外調人員和廠里的造反派輪番逼問她,要她承認參加了特務組織,并利用毛主席接見她搞陰謀。母親不承認,他們就脫下鞋用皮鞋底抽她的臉……回到“牛棚”時,母親的臉被打腫,嘴角流著血,目光呆滯,身體不停地顫抖。
當天晚上回到家里,母親被造反派勒令寫交代。也許她實在害怕即將到來的又一場羞辱與磨難,在黎明前最黑暗的一刻,她從四層樓的窗口跳了下去……母親的身體重重地落在樓下小菜場一個菜農的大菜筐里,當時尚有意識的母親還向圍上來的人們說出家里的門牌號碼——也許在那一刻,她還有一種本能的求生欲望,但等到有人找來黃魚車把她送到醫院時,已經沒救了。
那時候,她不知道我和哥哥的下落,追求革命的姐姐到上影廠給她貼了大字報,她身邊的那個男人也沒有為她遮擋一點點風雨。
那一年,母親只有48歲。
明星的誕生
上海,是母親結束生命的地方,也是她當年開始事業、轉變人生的地方。
1920年,母親出生在江蘇江陰長涇鎮,是家中第五個孩子,原名叫韋均犖,又叫韋亞君。舅舅的一位同學叫張大炎,是同鄉一富紳的兒子,他原來在上海美專學西洋畫,畢業后在蘇州做美術老師,母親也在那里上學。張大炎一直很喜歡比自己小九歲的同學妹妹,也照顧有加,不久母親有了身孕,他們結了婚。17歲那年,母親生下了我的哥哥,為此她中斷了學業,回家鄉做了富家的兒媳婦。我手里還有一張母親穿著泳衣,和張大炎在家鄉河里游泳的照片,可以看出,母親在當地確實屬于領風氣之先的人物。
1937年抗戰爆發,他們的家鄉被轟炸,我的一個姨媽被炸死,母親跟著張家逃難到了上海。剛到上海的母親,為謀生到巴黎大戲院(今準海電影院)邊上的何氏照相館當開票小姐。母親有南方女子的乖巧,又聰明大方,何氏照相館經理何佐民十分器重她。他從霞飛路上給母親買了時髦衣服,還為她拍了許多照片放在櫥窗里,以作招牌。
當時影業公司老板張善琨與紅極一時的女星童月娟因片酬產生矛盾,張老板故意想捧母親,準備讓她取代童月娟出演《王老虎搶親》。導演卜萬蒼覺得“韋均犖”的名字太拗口,于是給取了個“上官云珠”的藝名。雖然不久張老板與童月娟重歸于好,母親又被換了下來,但那也由此成為母親進入上海演藝界的起點。
后來,母親與反對自己演戲的張大炎的分歧越來越多。1940年,母親離了婚,張大炎帶著哥哥回到了老家。
第二年,母親拍攝了她的電影處女作《玫瑰飄零》,這一年又相繼拍攝了許多當時非常流行的“才子佳人”、“鴛鴦蝴蝶”類文藝片,開始在影壇嶄露頭角。
1942年,母親加入“天風劇社”,在此結識了成為她第二任丈夫的姚克。
姚克是蘇州人,早年畢業于耶魯大學,是20世紀30年代活躍于上海文壇的才子,回國后與魯迅來往密切。姚克后來熱衷于戲劇,1941年,他寫的《清官怨》吸引了很多著名演員加盟,雖然母親只在劇中演一個沒有幾句臺詞的宮女,卻吸引了名氣遠大于母親的姚克。1944年8月,母親生下了我的姐姐姚姚。
此時的母親,已是眾人眼里的大明星。她的事業一帆風順時,感情生活卻再一次遭遇危機——這一次問題出現在姚克身上。母親到天津、濟南、青島等地巡演時,姚克在上海愛上了一個富家女。母親聞訊后立即決定同姚克離婚,不滿兩歲的姚姚姐就跟了母親。
榮耀與辛酸
1951年,我的父親程述堯與母親在上海“蘭心大戲院”舉行婚禮,成為母親的第三任丈夫。
父親出生于北京一殷實之家,畢業于燕京大學,與黃宗江、孫道臨都是同學,也是學校文藝舞臺上的活躍分子。畢業后,父親在中國銀行做行長的英文秘書,有一份很不錯的薪水。
1946年,父親曾與黃宗英結婚。不久黃宗英去上海拍戲時結識了趙丹,向父親提出離婚。父親不甘心就這樣結束,從北京趕到上海。父親追到上海也沒有能挽救這一段婚姻,卻從此留在了上海,后來做了蘭心大戲院的經理。
1952年,全國開展“三反”運動,有人揭發父親貪污蘭心劇院的款項。父親平時就是大大咧咧的一個人,他以為數目不多,承認下來將錢補上就可以盡早擺脫麻煩,于是母親從家里拿出自己的800美元和兩個戒指送到劇院,作為“贓款”退賠。父親顯然太天真了,雖然這件事情后來被證明是誣告,但這樣一來,他就被徹底打上了“貪污犯”的標簽。
當時母親正為自己將從舊上海的明星脫胎為新中國文藝工作者而努力,為災區籌款義演、勞軍義演,她每次都積極參加,甚至勞累過度,得了肺病。此時此刻,她不能容忍父親的“錯誤”,于是堅決提出離婚。
父母離婚時,只有一歲多的我被判給父親。因為父親的再婚,四歲時,我被送回到北京的爺爺、奶奶家。
母親雖然不和我生活在一起,但我能感覺到她對我的寵愛。1962年,她來北京拍《早春二月》,母親把我接到劇組里,利用一切機會,增加母子之間的交流。
現在回想起來,在母親四十多歲時,她也許想到自己的未來,希望我和她在一起,母親對我的母愛也越來越多地流露出來。10歲那年我回了上海,周一至周六在母親家住,周日去父親家。那段時間,小時候沒有得到的母愛得到了些許補償:夏天洗完澡后,母親摟著我坐在陽臺上給我講故事,或是帶我和姐姐姚姚到附近散步。
母親斷斷續續給我寫過一些信,可惜這些信件,以及母親的照片后來都在“文化大革命”中燒毀了。父親去世后,我在整理他的遺物時,也看到了當年母親在臺歷上留給他的只言片語,這對我來說,是母親留給我的最后紀念。
(孟心媚摘自《現代家庭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