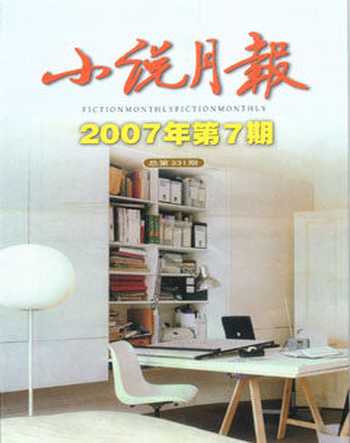吃飯去
煤氣灶上,這邊的鍋開了,那邊的鍋也開了,鍋蓋被掀下來,熱氣如狼似虎地向上躥。挨了煤氣灶,還有一只電磁爐,電磁爐上也坐了口鍋,里面的水也咝咝地響起來了。抽油煙機嗡嗡嗡的,聲兒大得能比過天上的飛機。可熱氣還是沒被它嚇倒,任性地躲了它,在不大的一點空間愈集愈多著。
胡小娟隔了窗玻璃向廚房望,熱氣將玻璃糊了一層,只隱約可見丈夫的身影。身影高大、胖壯,正背對了她,低頭在剁著什么,當當——當當——截東西被剁得飛起來,砰地撞著了玻璃,又落在了地上,胡小娟看清,那是一截蔥段。
胡小娟想,蔥段當然不必用那么大的力氣,倆人兒的飯更不必非用三口鍋不可,大劉他是有意的,有意要在廚房里鬧一鬧了。
胡小娟覺得很委屈,自打結婚,做飯的事就是大劉的,也不是一天兩天了,四十年都有了,四十年廚房里都風平浪靜的,現在大劉卻失去了耐心了。
這樣的“鬧”已有好些日子了,胡小娟卻也不好說什么,因為大劉每每從廚房里走出來,對她說“吃飯吧”的時候,并不見失去耐心的樣子。反是一臉的平和。胡小娟相信對那“鬧”的感覺,卻也不愿懷疑大劉的平和,但她還是敏感到,大劉那“吃飯吧”的前頭,已經將“小娟”省略掉了。這省略好像在“鬧”之前就出現了,她只是沒在意,六十多歲的人了,還小娟小娟的,不叫也罷。可是,她這里可以不在意,他那里就可以無緣無故地省略么?
大劉長有一副長臉龐,單看他的眼睛、鼻子和嘴巴,樣樣是說得過去的,可湊在他的臉上就十分地不理想了,他的臉太長了,還有一個肉乎乎的雙下巴,使臉上的東西就顯得有些零散,差了尺寸似的。特別是他的眼睛,與鼻子的距離拉得太長,而上面的眉毛又像他的頭發一樣又黃又稀,一對雙眼皮的大眼睛便顯得孤單單的,給人以莫名的突兀感。總之,不認識他的人,看他一眼通常是要吃一驚的;而認識他的人,往往又會生出幾分沒來由的憐憫來。相比較,胡小娟的長相倒自然了許多,她是小眼睛、小鼻子、小嘴巴,一張緊繃繃的小圓臉,個頭偏矮,身材偏瘦,腦后一把幾十年如一日的小刷子。胡小娟比大劉只小兩歲,但看上去卻像兩代人的樣子,大劉的長臉已長出了許多皺褶,而胡小娟除了眼角有少許的魚尾紋,臉側有淡淡的幾點黑斑,哪哪都還是飽滿的,透了光澤的。和大劉在一起,胡小娟倒從不感到尷尬,多少年來她已經習慣于對大劉的依賴了,在一個可依賴的人面前,他的長相如何到底是不重要的。
胡小娟離開廚房,在客廳的沙發上坐下來,翻起一本五十年代出版的外國小說。退休以后,她一直在搜集文學和醫學方面的舊書籍,大約有上千本了吧,她很是以此為榮。退休前她是一家報社的副刊編輯,她深信文學和醫學對人的重要,而舊書比新書又要可靠得多,因此對舊書的搜集,她看成是自個兒的一項重要工程。不過也很奇怪,她一邊覺得重要無比,一邊又沒耐心去讀完任何一本書,她只是翻一翻,一本書拿在手里至多三五分鐘,就要換上另一本了。這有點像她跟大劉學京戲,她總是向人贊美京戲的美妙,可又從沒耐心一字一句地學唱到底,學到艱深細微之處,她總是會說,哎呀不好了,肚子又疼了。她不是裝出來的,真的是疼,在她焦慮不安的時候她肚子就會疼,她的肚子敏感得,就像是和腦子連在一起似的。她知道,唱京戲她一輩子都休想趕上大劉了,大劉這人,學什么都不會肚子疼,退休以后,他硬是憑了幾盒磁帶,學會了幾十個唱段,雖說還差火候,但跟板眼唱下來是沒問題了。京戲這東西,她也深知它的好,可就是太難了,就像文學和醫學,多數的人,是只適合做一個欣賞者的。沒退休的時候,她也試著寫過小說,寫過詩歌、散文,還訂過中醫雜志,有時給自個兒開開藥方什么的,可哪一樣都是,做著做著就難了,一難肚子就疼起來了。還有這做飯,四十年她都不進廚房,也是因為肚子疼。肚子疼告訴她,做飯同樣是件難事,比起京戲,比起文學醫學的難度一點不在其下。好在,厚道的大劉容忍了她的肚子疼。幾十年如一日地擔當起了做飯的重任。他還從沒嫌棄過她的一事無成,在她偶爾自嘲的時候,他還安慰她說,你并沒有一事無成,有一件事你就成了。她問哪樣,他便說,讓一個男人為你做飯啊。她便大笑起來,笑著笑著卻又哭了,眼淚流了一串又一串的。大劉也不去在意,知道她淚窩兒淺,常常地說哭就哭。
這時,廚房那邊忽然有大劉的聲音傳過來:完了,完了完了!
胡小娟吃了一驚,問,什么完了?
大劉說,飯做不成了!
胡小娟說,怎么了?
大劉說,斷煤氣了!
大劉的聲音很高很急,但不知為什么,胡小娟總覺得那聲音里似還摻雜了興奮。
斷煤氣的事從前也不是沒有過,待上一會兒,很可能還會來的。但胡小娟還是從沙發上站起來,走到廚房,走到大劉的面前說,走吧,咱到兒子家吃午飯去!
他們的兒子劉壯壯,住在離這兒不遠的另一個小區里,不必坐車,步行走上六七分鐘就到了。他們已很長時間沒見到兒子了,兒子在機關忙,兒媳在學校忙,他們的孫子正上高中,晚上住在學校里,比他的老子們更忙。兒子倒是常給他們打電話,電話結束時總是說,哪天不想做飯了,就這兒吃來吧。雖說這樣的邀請只是隨口說說,但他們還是記在心里了,這一回,他們真是有再充足不過的理由了:煤氣沒了,飯做不成了,附近又沒有一家對口味的飯館,不去兒子家又去哪里呢!
兒子和兒媳,果然很高興地迎接了他們。看樣子兒媳也正在廚房做飯,看他們坐下來,轉身又到廚房去了。這個兒媳,自打和兒子結了婚,就沒讓兒子進過廚房,還總是今兒包餃子明兒烙餡兒餅地變換花樣,饅頭是她自個兒來蒸,面條是她自個兒來搟,肉是她自個兒來燉,外面的熟食她說一是費錢,二是吃了不放心,再說回到家里,也不能總盯了電視看啊。大劉曾感慨地對胡小娟說,世上竟還有這么喜歡做飯的女人。胡小娟沒吱聲,她想她能說什么呢,一個不能做飯的女人。不過她知道,兒媳是手有一份心也一份的,不管什么時候什么場合,她也不會甘心于服從的角色,她是喜歡別人來服從她的。有一回兒子從外面買了包子回來,她二話不說就扔到了垃圾袋里,兒子一氣之下跑到父母這邊,她竟也隨即跟了來,手里提了自個兒和好的面拌好的餡兒,硬是讓這三人放下快到口的飯菜,跟她一起包起餃子來了。
兒媳一個人在廚房忙活,這邊客廳里三個人說著話兒。
廚房那邊叮叮當當的聲音一陣一陣地傳過來,胡小娟隨了聲音不由得就站起來又坐下的。她去看大劉,見大劉反倒大腿壓了二腿,坐得穩如泰山一般。胡小娟只好說兒子,你去幫幫她吧。兒子說,不用,去了她反會不高興。胡小娟說,多兩口人吃飯呢。兒子說,多三口人也沒關系,您就放心吧。
果然,沒多大一會兒,廚房那邊就有香味兒飄過來了,隨即還伴了兒媳的喊聲:壯壯,叫爸媽吃飯了!
三人站起來往餐廳走。胡小娟注意到,大劉臉上有種掩飾不住的興沖沖的表情。胡小娟便說,看把你爸高興的。大劉說,怎么了?胡小娟說,應該祝賀你。
大劉說,祝賀什么?胡小娟說,終于吃上現成飯了。大劉說,是啊,不用進廚房就吃飯,誰不高興?胡小娟說,我早知道,你進廚房是不高興的。大劉說,你呀,讓壯壯評評理,我不高興能堅持四十年么?胡小娟說,不要提什么四十年,你那四十年無非是饅頭、米飯,米飯、饅頭。大劉說,嫌不好你來做呀,你為什么不做?
倆人都是笑著的,說出的話,卻是平時很少說過的。
倆人都有些奇怪,老了老了,在兒子面前倒有些任性起來了。兒子呢,不說話,只是笑。
接下來,是三人輪番到挨了餐廳的衛生間去洗手。洗完手,外面餐桌上的飯菜已擺好了,就見菜是四涼四熱,色澤鮮亮,氣味誘人;飯是白米飯,盛在三只精致的藍花瓷碗里;湯是酸辣豆腐湯,滿滿的一盆,熱氣騰騰,香氣撲鼻。不過,怎么只盛了三碗米飯呢?正疑惑間,就見兒媳一轉身進了衛生間,啪嗒一聲,好像還從里面上了鎖。胡小娟只當兒媳要方便,便示意大劉先別動筷子,老老實實地坐在那里等。
一會兒,從衛生間傳出了水聲——嘩啦嘩啦——竟是持續不斷。
胡小娟和大劉相互望望,又都去望兒子。
壯壯沖了衛生間喊,今兒不洗了不行嗎?
衛生間的兒媳也喊,不行!
壯壯沖父母笑笑,說,甭管她,咱先吃吧。
胡小娟說,她在洗澡?
壯壯說,不洗澡不能吃飯。
胡小娟說,等洗完不都涼了?
壯壯說,涼了再熱唄。
胡小娟說,這幾時有的習慣?
壯壯說,早了,兒子一住校就有了。
胡小娟說,我們要不在呢,不在你等不等她?
壯壯老實地回答,全在她了,她說等就等,她說不等就不等,反正也不是什么大事。
胡小娟不由得哼了一聲,說,聽聽,還不是什么大事。
胡小娟有些賭氣似的首先拿起了筷子。接著大劉和壯壯也將筷子拿了起來。
三人都沒再說什么話,默默地吃飯,默默地聽著嘩啦嘩啦的水聲。兒媳的手藝挺不錯,比大劉做得好吃多了。大劉顯然很愛吃,一口接一口的,嘴張得很大,腮幫子鼓鼓的。劉壯壯也是沒心沒肺的樣子,將碗端起來,撲撲拉拉地往嘴里送。胡小娟坐在他們的對面,覺得人吃飯的時候其實是很丑的,特別是大劉,嘴張開的時候那張臉更長了,就像個怪物一樣。她移開目光,有點不忍心再看他們。
嘩啦嘩啦——吧嗒吧嗒——嘩啦嘩啦——吧嗒吧嗒——
胡小娟忽然覺得有點肚子疼,她放下筷子,再也不想吃下去了。
倆人回到家里,胡小娟到自個兒的床上躺著去了。每回肚子疼,她不吃藥,不看醫生,就這么躺上一會兒便過去了。大劉知道她的毛病,也不去理她,顧自躲在自個兒的房間里聽京戲。學京戲是要時間的,聽一會兒是一會兒,學一句是一句,他學會的幾十個段子,就是這么一分一秒地學來的。過去在工廠的時候就是這樣,他不怕吃苦,勤于學習,從一個普通工人一直干到了車間主任。胡小娟就是他當車間主任的時候有人介紹給他的。那時胡小娟大學畢業剛分到報社,而他只是初中學歷。可喜的是,胡小娟竟是對他滿意,她說,她喜歡他的踏實肯干,喜歡他的高大結實,有這么個人在身邊,她一輩子都會心安的。那時他也想對她說,他喜歡有知識有文化的人,還喜歡她腦后的小刷子,一見到那小刷子他就心跳不止。可這話,直到現在他也沒好意思說出來過。現在,胡小娟的小刷子還在,他卻早已不會心跳了,胡小娟呢,似也沒了那些年的心安了,年歲愈大,心眼兒反倒愈小起來了,動不動就肚子疼,一肚子疼就要跟他分開睡。這些年,她和他幾乎都夠得上分居了。
大劉學的是《林沖夜奔》里的一段唱:大雪飄,撲人面,朔風陣陣透骨寒。彤云底鎖山河暗,疏林冷落盡凋殘。往事縈懷難排遣,荒村沽酒慰愁煩……這段唱腔好,詞好,當紅的老生于魁志唱得也好,學著學著,大劉竟是鼻子一酸,眼睛有些淚花花的了。他心里笑自個兒,動的哪門子情啊,人家林沖冤情深似海,你的冤情在哪里呢?
過了一會兒,大劉出來上廁所,忽聽得胡小娟的房間里有嗚嗚的哭聲。大劉先沒在意,上完廁所出來,卻聽那哭聲忽然變成了號啕大哭了,哇——哇哇——
大劉便有些吃驚,這樣的哭,胡小娟很少有過呢!她哭的是哪一出呢?
大劉在門外轉來轉去的,到底也沒敢推開胡小娟的房門。好容易聽得哭聲止住了,正要進去,倒見胡小娟走了出來。
胡小娟自是兩眼通紅,臉上掛滿了淚痕,也不看大劉,低了頭就奔衛生間去了。
過了一會兒又一會兒的,衛生間的門終于開了,胡小娟臉上的淚痕不見了,眼睛卻仍是紅的,她從大劉眼前走過去,徑自進自個兒的房間,穿了件外出的衣服走出來。
大劉開口問,你去哪兒?
胡小娟說,吃飯去。
大劉說,哪兒吃飯去?
胡小娟說,彬彬家。
大劉說,不是吃過了?
胡小娟說,吃晚飯。
大劉說,怎么了?
胡小娟說,不怎么。
大劉說,到底怎么了?
胡小娟說,不怎么。
大劉說,你呀,就別鬧了好不好?
胡小娟忽然冷笑道,是我鬧還是你鬧了?
大劉說,我鬧什么了?
胡小娟說,你天天在廚房鬧,以為我覺不出來?
大劉說,我在廚房鬧,還天天?操!
胡小娟說,聽聽,人都罵上了。
大劉說,胡小娟,你是不是把在壯壯家說的話當真了?
胡小娟說,聽聽,我都改胡小娟了。
大劉說,你不叫胡小娟嗎?
胡小娟說,我是叫胡小娟。
大劉說,胡小娟你都要把我氣蒙了,要真拿那些話當真,不高興的也該是我,別忘了話是你先提起來的!
胡小娟說,甭說那話不話的,我不過是到彬彬家吃頓飯,省得你給做了。
大劉說,我都做了四十年飯了,還在乎這一頓飯嗎?
胡小娟說,又是四十年的飯。
大劉說。是四十年!
胡小娟說,四十年怎么了?
大劉說。胡小娟,你不要逼我!
胡小娟說,你想說什么?盡管說出來!
大劉說,胡小娟,你這么逼我,我恨你!
胡小娟說,你恨我,好,到底說出來了,我早知道,早知道你恨我,從不叫小娟的時候我就知道了。
大劉說,一個名字你就在乎了,我呢,一個大活人一天三回鉆進廚房里,你在乎過嗎?你進廚房看過我一眼沒有?
胡小娟不由得怔了一下,但還是不肯認輸地回應道,我跟你不一樣,不看你不是因為恨你,是因為厭惡你!
大劉說,好,你也到底說出來了,你厭惡我,一個女人整天吃著男人做的飯,還說厭惡這個男人!胡小娟說,我是整天吃著你做的飯,可我就是厭惡,厭惡你做飯,厭惡你吃飯,厭惡你那丑八怪的樣子!
大劉說,滾,你給我滾!
彬彬是胡小娟和大劉的女兒,住在城市的另一頭,之間有17路公交車連接起來。胡小娟不喜歡17這個數字,每回去女兒家,幾乎都會有一場不愉快發生,她總覺得和這17有關。
彬彬見到母親,先是吃了一驚,隨即就說,怎么沒打個電話來?胡小娟說,放心,吃完晚飯我就走,不
誤你的事的。彬彬說,看您說什么呢,又小心眼兒了。
彬彬是一位專職作家,為了寫作至今孩子都沒肯要,時間對她是第一重要的。
坐下來,胡小娟還是把跟大劉吵架的事說了一遍。說的時候,她還是忍不住哭了。她知道女兒是不會理解她的,女兒只理解她書里的人。果然,女兒聽完沒哭,反倒哈哈地笑起來了。
胡小娟惱火地說,你笑什么?
彬彬說,您當真說我爸是丑八怪了?
胡小娟說,說了。
彬彬說,您當真厭惡我爸?
胡小娟說,當真。
彬彬說,我不信。
胡小娟說,為什么不信?
彬彬說,因為您沒肚子疼啊。
胡小娟說,又胡說了。
彬彬說,您想啊,厭惡一個人,還要跟他日夜廝守著,這是多大的折磨,可您那敏感的肚子,怎么就從沒為這疼過呢?
胡小娟說,你怎么知道沒疼過?
彬彬說,疼過嗎?
胡小娟怔了一會兒,想想與大劉在一起的這些年,忽然就覺得,她所有的肚子疼,仿佛都與她和大劉在一起的日子分不開似的,這難那難,最大的難,也許正是這些日子呢!但即便這么想想,她也覺到了一種令她懼怕的難度。于是,她便懶得再想下去,只對女兒說,這是筆糊涂賬,我也說不清了。
這么說著,胡小娟竟真的覺得肚子又絲絲拉拉地疼起來了。這時,她十分渴望往里填些東西,便說,彬彬,早些做飯吧,這星期該誰做了?
做飯的事,彬彬和丈夫是一遞一星期來承擔的。彬彬告訴胡小娟,是丈夫的星期,他就快下班回來了。胡小娟說,要不是肚子疼,我就進廚房做去了。彬彬笑道,別逗了,您進廚房,除非日頭從西邊出來。
彬彬又坐到電腦桌前去了,一點沒做飯的意思。胡小娟知道女婿是個喜歡斤斤計較的人,多了口人吃飯,彬彬還不幫他,他會不高興的。對這女兒,胡小娟也十分地不滿意,她心里就惦了寫作了,話還沒說幾句,就又要去打字了。往日來這兒待兩天,電視不讓看,音響不讓開,咳嗽重了她都皺眉頭,更不要說陪了說說話兒了。胡小娟想,還作家,自個兒家人的心思都弄不懂,算哪門子的作家呀。
彬彬兩手撫在鍵盤上,果然噼里啪啦地打起字來了。
胡小娟坐在女兒身后的沙發上,只能看到女兒的后背。
噼里啪啦噼里啪啦——
時間一分一秒地過去,漸漸地,天黑下來了,屋里暗起來了。
噼里啪啦噼里啪啦——
胡小娟覺得,女兒已是將她這個媽忘記了。她的淚水在眼眶里打著轉兒,卻又慶幸著女兒給她的后背,這使她有機會悄悄地站起來,悄悄地走向門口,悄悄地打開門走了出去。她將門關得死死的,生怕女兒追出來似的。她仿佛聽到女兒在屋里喊,媽,干嗎去呀?不是要在這兒吃晚飯嗎?
街上的路燈已經亮起來了,兩邊的鋪面也閃了五顏六色的光亮,鋪面前的榕樹上,綴了無數小星星一般的彩燈,飛馳而過的車輛,不停地將燈光打在樹上,忽明忽暗,忽明忽暗……
這燈的世界,胡小娟已看了許多年了,實在沒什么好看的了,但她還是沒有馬上去坐公交車,她沿了一家一家的玻璃櫥窗慢慢走著,邊走邊看,仿佛一個閑在的無憂無慮的女人。但她的心里卻在想,今天的晚飯,該去哪里吃呢?
胡小娟回到家的時候,已是晚上9點鐘了。她看到大劉蜷在沙發上,瞇了眼睛,像是睡著了;廚房里,仍是去兒子家之前的樣子,三口鍋坐在灶上,冷冰冰的。看來,他晚飯是吃也沒吃,做也沒做呢!這時,大劉仿佛覺到了胡小娟的存在,他睜開眼睛,睡眼惺忪地問道,吃飯了嗎?
胡小娟正往自個兒的房間走,聽到問話,忽然鼻子一酸,眼圈一下子就紅了。
原本,胡小娟是做了最壞的打算的,她想,如果他不想再做下去了,她就雇個保姆來做;如果他不想再過下去了,她就同他分開來過。
胡小娟停在自個兒房間的門口,背對了大劉答道,沒呢。
大劉說,我也沒吃,我這就做去。
大劉竟是真的到廚房去了。
灶火著起來了。
抽油煙機響起來了。
鍋里的熱氣冒起來了。
大劉在熱氣中晃來晃去的。胡小娟看在跟里,臉上的淚水愈來愈多了。
要不是臉上的淚水,胡小娟幾乎不敢相信眼前的一切,至少要有一場鄭重的談話吧?至少要有一次深刻的反省吧?至少要對那“恨”呀、“厭惡”呀做一做解釋吧?可什么也沒有,什么也沒有就一切都似煙消云散了。
后來,胡小娟還鬼使神差地跑到廚房去了,自個兒拿了一頭大蒜,不做聲地剝著。
大劉看看她,也沒有做聲。
胡小娟一邊奇怪著自個兒,一邊又有些不甘心,她想,等飯做好了,抽油煙機停了,廚房里安靜下來了,她還是要問一問大劉,“我恨你”,到底是怎么一回事?不過同時她又有些擔心,要是大劉問她“厭惡”是怎么回事,她又該如何回答他呢?
原刊責編李浩
[作者簡介]何玉茹,女,河北省石家莊人,1986年畢業于廊坊師專中文系,1976年開始發表作品,其中篇小說《綠》獲河北省文藝振興獎,著有小說集《她們的記憶》。本刊曾選發過其短篇小說《孤點》、《真實背景》、《一個叫李文娟的女人》等。現在河北省某刊物任職,河北省作家協會會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