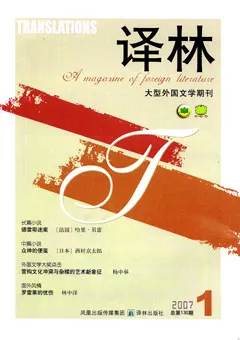營(yíng)構(gòu)文化沖突與雜糅的藝術(shù)新象征
2006年10月12日,瑞典皇家科學(xué)院諾貝爾獎(jiǎng)委員會(huì)宣布將年度諾貝爾文學(xué)獎(jiǎng)授予土耳其作家?jiàn)W爾罕·帕慕克(Ferit Orhan ㏄amuk)。瑞典文學(xué)院在授獎(jiǎng)公報(bào)中稱(chēng)帕慕克獲獎(jiǎng)的理由是“在追求他故鄉(xiāng)憂(yōu)郁的靈魂時(shí)發(fā)現(xiàn)了文明之間的沖突和雜糅的新象征”。 這一評(píng)語(yǔ)準(zhǔn)確道出了帕慕克生活與創(chuàng)作的真實(shí)狀態(tài)。
1952年6月7日,帕慕克出生于土耳其伊斯坦布爾市尼森塔斯區(qū)一個(gè)富有的工業(yè)主家庭,小時(shí)候的帕慕克給同學(xué)的印象是懶散、貪玩、好惡作劇,從六歲開(kāi)始學(xué)繪畫(huà),一直學(xué)到二十二歲,對(duì)他后來(lái)的寫(xiě)作產(chǎn)生了極大影響。帕慕克的中學(xué)教育是在羅伯特學(xué)院完成的,它是美國(guó)人在伊斯坦布爾辦的第一所學(xué)校。1967年帕氏進(jìn)入伊斯坦布爾科技大學(xué)學(xué)習(xí)建筑專(zhuān)業(yè),他的家庭希望他能像祖父和父親那樣成為一名工程師或建筑師。但三年后,他認(rèn)為自己的興趣不在當(dāng)工程師上,就主動(dòng)退學(xué),但是他不樂(lè)意到政府的軍隊(duì)里服兵役,于是申請(qǐng)到伊斯坦布爾大學(xué)新聞學(xué)院學(xué)習(xí),并于1974年停止了繪畫(huà),正式開(kāi)始寫(xiě)作生涯。1977年于伊斯坦布爾大學(xué)新聞學(xué)院畢業(yè),同樣是為了躲避服兵役,他又申請(qǐng)碩士學(xué)位繼續(xù)學(xué)習(xí)。大學(xué)的最后一年,他的生活發(fā)生了一系列大變化,使得他同來(lái)自土耳其上流社會(huì)家庭的一些朋友格格不入,也使得他走向了寫(xiě)作之路,他后來(lái)回憶說(shuō):“我開(kāi)始形成自己獨(dú)立的世界,我認(rèn)為這是我家庭環(huán)境造就的,家里無(wú)聊的談話(huà)、爭(zhēng)吵沒(méi)完沒(méi)了,我被這些接連不斷的事件影響著,盡管在土耳其有百分之七八十的家庭都是如此,但我父母還是不能忍受,于1972年開(kāi)始分居,到1978年正式離婚。1979年,我父親再婚,因父親這段時(shí)間居住在美國(guó),我同母親生活在一起,并開(kāi)始寫(xiě)一部小說(shuō)。母親并不理解我。試想你在寫(xiě)一部小說(shuō),一部你生活感覺(jué)的小說(shuō),一部你存在的目的的小說(shuō),他們卻在這困苦的時(shí)刻使你相信它不過(guò)是件荒誕的事,沒(méi)有一個(gè)正常的人會(huì)從中獲益。可以說(shuō)那是些艱難的歲月,父親更寬容些,與母親的方式相比積極一點(diǎn)。有許多事情引發(fā)我去創(chuàng)作,比如,我從沒(méi)有一個(gè)我喜歡的女朋友,我不能吸引女孩子的注意,家里人也沒(méi)有一個(gè)人注意我。因?yàn)檫@一切,我要寫(xiě)作,以顯示我是┧……”這樣,帕慕克在孤獨(dú)和寂寞中開(kāi)始了創(chuàng)作生涯,邊寫(xiě)邊讀,他心儀的作家有普魯斯特、薩特、博爾赫斯、伍爾夫、福克納、亨利·詹姆斯,還有后殖民理論家愛(ài)德華·賽義德等。
1982年是帕慕克一生關(guān)鍵的一年。這一年他與一個(gè)出身于俄羅斯家庭的姑娘阿依琳·特里根結(jié)婚,阿依琳一家在俄國(guó)革命期間移民土耳其,這位俄羅斯裔姑娘是唯一理解、支持帕氏創(chuàng)作的人。婚后多年,由于阿依琳在大學(xué)就讀,一直沒(méi)要孩子,直到1991年他才生有一女兒,按照帕慕克的意愿,取名字叫“露雅”——土耳其語(yǔ)意為“夢(mèng)想”,表達(dá)了自己對(duì)寫(xiě)作和人類(lèi)不同文明相互關(guān)系的期望。但同帕慕克的父母一樣,這對(duì)夫婦2001年又解除了婚姻。1982年發(fā)生在帕慕克身上另外一件重要的事是出版了處女作《塞夫得特州長(zhǎng)和他的兒子們》,此作寫(xiě)于1979年,原名為《黑暗與光明》,獲米利耶特出版社小說(shuō)競(jìng)賽獎(jiǎng),1983年小說(shuō)獲得奧爾罕·凱馬爾小說(shuō)獎(jiǎng),這對(duì)帕慕克來(lái)說(shuō)是一個(gè)遲到的成功,也是他實(shí)現(xiàn)成為出色小說(shuō)家的理想的開(kāi)始。小說(shuō)以帕慕克生活成長(zhǎng)的伊斯坦布爾尼森塔斯區(qū)為背景,寫(xiě)了一個(gè)富有的伊斯坦布爾家庭三代人的故事,三代人的歷史命運(yùn)表現(xiàn)了土耳其人逐漸被財(cái)富和西方文化所浸染的過(guò)程,從中讀者可以看到帕慕克家庭的影子,具有明顯的自傳性。也就是從這部處女作開(kāi)始,帕慕克關(guān)注起西方文化對(duì)土耳其的影響,伊斯蘭文明同西方文明的關(guān)系,在多部作品中構(gòu)建起表現(xiàn)文明沖突與雜糅的藝術(shù)新象征。
1983年帕慕克出版第二本小說(shuō)《寂靜的房子》,被譯成法語(yǔ)流行歐洲,于1991年獲得歐洲發(fā)現(xiàn)獎(jiǎng)。這是一部帶有伍爾芙、福克納小說(shuō)特點(diǎn)的小說(shuō),以五種視角對(duì)往事進(jìn)行回憶。小說(shuō)故事之一回憶了最后一位土耳其蘇丹統(tǒng)治時(shí)期,一位醫(yī)學(xué)家編輯了一部四十八卷的百科全書(shū),它的價(jià)值足以使得土耳其這樣一個(gè)農(nóng)業(yè)國(guó)家的文明同西方國(guó)家文明相抗衡,但是1928年,由于土耳其實(shí)行語(yǔ)言改革,他用土耳其語(yǔ)寫(xiě)的手稿被廢止,變得毫無(wú)用處,一些學(xué)者、藝術(shù)家同樣生活在危機(jī)、邊緣之中。這一細(xì)節(jié)表明,徹底拋棄土耳其文化與語(yǔ)言獨(dú)立性的荒誕可笑。
1985年出版第一本歷史小說(shuō)《白色城堡》,譯成英語(yǔ)在美國(guó)上市后,使他享譽(yù)全球,紐約時(shí)報(bào)書(shū)評(píng)稱(chēng)他是“一位新星正在東方誕生”,1990年獲美國(guó)外國(guó)小說(shuō)獨(dú)立獎(jiǎng)。小說(shuō)敘述了一個(gè)來(lái)自威尼斯的奴隸與一個(gè)奧斯曼土耳其學(xué)者的故事,兩個(gè)人物性格不同,土耳其學(xué)者富有冒險(xiǎn)、沖動(dòng)精神,尊敬科學(xué)與理性,意大利奴隸無(wú)名無(wú)姓,是個(gè)夢(mèng)想家、講故事的人、本能地生存者,兩個(gè)人物爭(zhēng)相比較各自遵奉的文明、文化的優(yōu)點(diǎn),不幸的是他們都十分關(guān)心戰(zhàn)爭(zhēng)科學(xué),土耳其學(xué)者利用從奴隸那里學(xué)來(lái)的機(jī)械知識(shí),為蘇丹制作了一個(gè)攻打歐洲的重武器,但是它在波蘭瓦爾特關(guān)隘深陷泥沼,最后失敗,這一象征性的歷史細(xì)節(jié)展示了歷史上土耳其帝國(guó)軍事上的失敗,也批判了人們對(duì)知識(shí)的濫用、對(duì)不同文化的暴力與破壞行為,展現(xiàn)了歐洲文明與伊斯蘭世界的交流與融合等重大問(wèn)題。最后,土耳其學(xué)者與威尼斯奴隸相互更換了衣服與身份,變?yōu)橥炼鋵W(xué)者的奴隸消失在大霧之中,而變成奴隸的土耳其學(xué)者來(lái)到威尼斯,就像那個(gè)真實(shí)身份的意大利人適意地生活在那里,但回到自己家里又過(guò)著原來(lái)土耳其學(xué)者的生活,在每一個(gè)環(huán)境中生活都能自如適應(yīng)。作者通過(guò)兩個(gè)不同文化文明背景人物身份彼此互換的象征,批判了一種文化吃掉、戰(zhàn)勝另一種文化的行為思想,一種文化比另一種文化優(yōu)越的謬論,表現(xiàn)出不同文化文明相互借鑒與融合、共同存在的可能性。
1983—1988年,帕慕克攜同妻子去美國(guó),在美國(guó)紐約城哥倫比亞大學(xué)和依荷華大學(xué)做了三年的訪問(wèn)學(xué)者,并開(kāi)始小說(shuō)《黑書(shū)》的寫(xiě)作,此書(shū)于1990年在伊斯坦布爾出版,這本小說(shuō)讓他在土耳其文學(xué)圈備受爭(zhēng)議,同時(shí)也廣受一般讀者喜愛(ài),法文版獲得了法蘭西文化獎(jiǎng)。1992年他以這本小說(shuō)為藍(lán)本,完成《隱蔽的臉》的電影劇本。小說(shuō)描寫(xiě)了一個(gè)年輕的律師在妻子失蹤后的生活故事,向讀者展現(xiàn)了古老的伊斯蘭生活和文化的細(xì)節(jié)。此書(shū)以其華麗的句子、后現(xiàn)代風(fēng)格、模棱兩可的政治態(tài)度和輕微的諷刺語(yǔ)調(diào)獲得成功,也倍受指責(zé),還引起了土耳其左翼分子與先驗(yàn)主義者的不滿(mǎn);同時(shí),這部作品又體現(xiàn)了他一貫善于表現(xiàn)的二元對(duì)立主題:東方與西方,同一性與差異性,群體與個(gè)體,虛構(gòu)與真實(shí),意義的確定性與模糊性等這些人類(lèi)在探討文化身份時(shí)普遍存在的方面。
1995年《新人生》一書(shū)的出版在土耳其造成轟動(dòng),成為土耳其歷史上銷(xiāo)售速度最快的書(shū)籍,被譽(yù)為現(xiàn)代土耳其文學(xué)最偉大的作品之一。小說(shuō)主要描寫(xiě)了土耳其大學(xué)生的生活,講述一個(gè)大學(xué)生迷上了一個(gè)全神貫注地讀書(shū)的姑娘,也愛(ài)上了她讀的那本書(shū),閱讀改變了二人的生活和世界,這對(duì)年輕的戀人踏上回歸故鄉(xiāng)的自由之旅,一路上深切體會(huì)了西方現(xiàn)代性文化影響下土耳其文化傳統(tǒng)的失落,他們被這一切所困擾,后來(lái)年輕的大學(xué)生懷抱著書(shū)卷,以一個(gè)藝術(shù)家的方式——“一種西方文化的偉大發(fā)明”(讓讀者想起少年維特的方式),結(jié)束了自己的生命,通過(guò)這種方式他試圖回到國(guó)家、民族的歷史中去尋找新生活,擺脫文化傳統(tǒng)“失憶癥的困擾”。
1998年《我的名字叫紅》出版,這本書(shū)確定了他在國(guó)際文壇上的地位,他由此獲得了2003年都柏林文學(xué)獎(jiǎng),獎(jiǎng)金高達(dá)十萬(wàn)歐元,同時(shí)還贏得了法國(guó)文藝獎(jiǎng)和意大利格林扎納·卡佛文學(xué)獎(jiǎng)。
2002年發(fā)表小說(shuō)《雪》。這是一部關(guān)于土耳其東部城市雪城——卡爾斯市政治生活的小說(shuō),廣泛展現(xiàn)了土耳其伊斯蘭教眾、軍隊(duì)、世俗政黨之間的緊張關(guān)系,表現(xiàn)了庫(kù)爾德民族主義者與土耳其民族主義者之間的劇烈沖突。小說(shuō)問(wèn)世后引起很大反響,帕慕克則聲稱(chēng)這是他“第一本政治小說(shuō),也是最后一本政治書(shū)籍”。小說(shuō)作者通過(guò)一位到訪的帶有西方背景的詩(shī)人的眼光,發(fā)現(xiàn)作為一個(gè)土耳其藝術(shù)家會(huì)覺(jué)得同東西方兩種文明都有深刻的聯(lián)系,對(duì)哪一邊表示效忠都不可能。這也表現(xiàn)了作者自身的狀態(tài)。加拿大女作家瑪格麗特·阿特伍德評(píng)論說(shuō):“一如帕慕克的其他小說(shuō),《雪》是一個(gè)分裂的、滿(mǎn)懷希望的、孤獨(dú)而神秘的土耳其靈魂的一次深度之旅。”它有著“游戲式的鬧劇,可怕的悲劇間的界限非常精妙,是一本男性迷宮小說(shuō)”。
2003年發(fā)表《伊斯坦布爾:城市記憶》,作品主要回憶作者自己一家在伊斯坦布爾的生活史,表達(dá)了對(duì)故鄉(xiāng)的無(wú)限熱愛(ài)之情,書(shū)中插入了不少帕慕克家庭人員的黑白照片,增強(qiáng)了作品的時(shí)間感和沉思情調(diào),帶有突出的自傳特色。2005年該作獲得德國(guó)書(shū)業(yè)和平獎(jiǎng),同時(shí)獲諾貝爾文學(xué)獎(jiǎng)提名。
除此之外,從20世紀(jì)90年代開(kāi)始,帕慕克還寫(xiě)了一系列有關(guān)人權(quán)的文章,一些有關(guān)自由和少數(shù)種族問(wèn)題的演講稿,其中的觀點(diǎn)與土耳其主流政治意見(jiàn)不合拍,在某些方面還批評(píng)國(guó)家政策,這些文章加上一部分日記,于1999年結(jié)集為《別樣的顏色》出版。
目前,帕慕克的作品已被譯成四十多種語(yǔ)言出版。西方批評(píng)界把他和普魯斯特、托馬斯·曼、卡爾維諾、博爾赫斯、安伯托·艾柯等大師相提并論。
從思想上看,帕慕克作品主要表現(xiàn)了東西方文明的沖突與交織,從藝術(shù)上看,帕慕克是公認(rèn)的當(dāng)代土耳其最具后現(xiàn)代主義風(fēng)格的小說(shuō)家,同時(shí)他又雜糅進(jìn)許多伊斯蘭傳統(tǒng)藝術(shù)、現(xiàn)實(shí)主義的因素,成為獨(dú)具一格的小說(shuō)家。這些思想傾向與藝術(shù)的特點(diǎn)突出表現(xiàn)在《我的名字叫紅》中。
小說(shuō)以16世紀(jì)末奧斯曼帝國(guó)為背景,圍繞土耳其蘇丹宮廷細(xì)密畫(huà)師高雅被殺事件,分五十九個(gè)敘述單元,講述了一個(gè)錯(cuò)綜復(fù)雜的故事,作者把高超的現(xiàn)代、后現(xiàn)代藝術(shù)同經(jīng)典的小說(shuō)敘事方法結(jié)合,營(yíng)造了一部兼容歷史小說(shuō)、哲理小說(shuō)、偵探小說(shuō)、愛(ài)情小說(shuō)、心理小說(shuō)、迷宮小說(shuō)等于一體的百科全書(shū)式作品。小說(shuō)每一章更換一個(gè)敘述者,都以第一人稱(chēng)自稱(chēng),每一章的標(biāo)題含有“我”:1.我是一個(gè)死人;2.我的名字叫黑;3.我是一條狗;4.人們將稱(chēng)我為兇手……,這里的敘述者既有活人、死人,也有動(dòng)物、植物,每一個(gè)敘述者都是主人公,又都不是主人公,換言之,敘事群體才是主人公,他們的講述共同構(gòu)成完整的故┦隆—1591年,伊斯坦布爾。一位蘇丹的細(xì)密畫(huà)師高雅被人謀殺,尸體被拋入深井。畫(huà)師生前接收了一項(xiàng)蘇丹的秘密委托,與其他三位當(dāng)朝最優(yōu)秀的細(xì)密畫(huà)師齊聚京城,分工合作,用歐洲的畫(huà)法——透視法繪制一本曠世之作,頌揚(yáng)蘇丹的生活與帝國(guó)。他的死亡顯然與這項(xiàng)秘密任務(wù)有關(guān)。此時(shí)書(shū)中的一位敘述者“黑”回到了闊別十二年的故鄉(xiāng),他在經(jīng)受了愛(ài)情的波折、東西方不同的繪畫(huà)藝術(shù)為象征的文化洗禮之后,查清了殺人兇手是三位著名畫(huà)師中藝名叫“橄欖”的,終于獲得了多年前相愛(ài)的女人謝庫(kù)瑞的愛(ài)情。謝庫(kù)瑞的小兒子奧爾罕長(zhǎng)大后,成了一名作家,把這一兇殺故事和父母的傳奇故事寫(xiě)下來(lái),講給讀者聽(tīng),成了這部小說(shuō)。
從每個(gè)敘述者講故事的風(fēng)格看,帕慕克使用了古典的伊斯蘭文學(xué)技巧,也運(yùn)用19世紀(jì)歐洲現(xiàn)實(shí)主義小說(shuō)處理細(xì)節(jié)的方法,還具備現(xiàn)代主義與后現(xiàn)代主義的手法。這使得小說(shuō)具有了傳統(tǒng)講故事的天然靈韻,又有著后現(xiàn)代小說(shuō)高奇的技巧,英國(guó)《出版人周刊》評(píng)論《我的名字叫紅》是“以酒館說(shuō)書(shū)人的遣詞用字?jǐn)⑹鲆粍t歷史懸疑故事……帕慕克擁有迷人的藝術(shù)天賦和邪靈般的智慧”。在談到自己的敘事藝術(shù)時(shí),帕慕克認(rèn)為:“實(shí)際上不停地扮演不同的人物以第一人稱(chēng)的方式說(shuō)話(huà)非常有趣。我不斷地發(fā)掘各種聲音,包括:一位16世紀(jì)奧斯曼的細(xì)密畫(huà)師的聲音,一位苦苦尋找戰(zhàn)場(chǎng)上失蹤丈夫的兩個(gè)孩子的母親的聲音,殺人兇手的可怕聲音,一個(gè)死人在去往天堂的路上發(fā)出的聲音等等。”這種多聲部合唱的復(fù)調(diào)藝術(shù)特征,堪與伍爾芙、福克納、陀思妥耶夫斯基相媲美。對(duì)此敘事風(fēng)格,迪克·戴維斯在《泰晤士報(bào)文學(xué)副刊》撰文認(rèn)為:“《我的名字叫紅》就像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卡拉馬佐夫兄弟們》一般,超越原有的界線,雖然是以古典的伊斯蘭文學(xué)技巧來(lái)說(shuō)故事,卻富含19世紀(jì)歐洲小說(shuō)處理細(xì)節(jié)的方法。帕慕克的小說(shuō)技法融合東方的與西方的兩種技藝,而且在兩者之間游刃有余并具獨(dú)創(chuàng)性。”
從小說(shuō)營(yíng)構(gòu)的藝術(shù)象征看,揭示殺人之謎的過(guò)程就是一個(gè)大的藝術(shù)象征,“橄欖”之所以殺死高雅畫(huà)師和另一位叫“長(zhǎng)者”的畫(huà)師,表面上表現(xiàn)了東西方繪畫(huà)藝術(shù)的沖突,內(nèi)里表現(xiàn)的是伊斯蘭文化與歐洲文化、東方與西方文化之間的沖突。他所掌握的傳統(tǒng)細(xì)密畫(huà)法與文藝復(fù)興的透視畫(huà)法形成了沖突,這樣,如何協(xié)調(diào)傳統(tǒng)與外來(lái)因素之間的對(duì)抗,如何看待過(guò)去與現(xiàn)在的沖突就成為一個(gè)異常重要的問(wèn)題,這恰恰就是不同文化與文明碰撞、相遇、交流所要認(rèn)真處理的問(wèn)題。“橄欖”之所以成為兇手,是他的內(nèi)心受到了強(qiáng)烈的文化沖擊的結(jié)果,是他不能合理處理兩種畫(huà)風(fēng)的結(jié)果。對(duì)此現(xiàn)象,帕慕克認(rèn)為:“對(duì)傳統(tǒng)的伊斯蘭畫(huà)師而言,西方肖像畫(huà)的繪畫(huà)方式是個(gè)極大的挑戰(zhàn),這與他們傳統(tǒng)的繪畫(huà)方式完全不同。基于此,代表了兩種完全不同的觀看、繪畫(huà)方式,甚至代表了兩個(gè)不同的世界。一個(gè)通過(guò)個(gè)人的研究觀看,另一個(gè)通過(guò)神之眼觀看世界。后者更像是用精神之眼在解讀世界。在我的小說(shuō)里,這種沖突甚至帶來(lái)了兇殺。但是讀者應(yīng)該發(fā)現(xiàn),我并不相信存在這樣的沖突。在我看來(lái),所有優(yōu)秀的藝術(shù)品都來(lái)自不同文化的混合。”
從小說(shuō)細(xì)節(jié)描寫(xiě)看,小說(shuō)本身就以文字繪出了一幅“細(xì)密畫(huà)”。帕慕克從六歲到二十二歲一直學(xué)習(xí)繪畫(huà),對(duì)繪畫(huà)藝術(shù)有較深的了解,他構(gòu)思這部作品時(shí)有意引入了細(xì)密畫(huà)的方法:“激發(fā)我寫(xiě)作這本書(shū)激情的主要是伊斯蘭細(xì)密畫(huà)。我把我看過(guò)的細(xì)密畫(huà)里不可勝數(shù)的細(xì)節(jié)都放在了小說(shuō)里。在愛(ài)和戰(zhàn)爭(zhēng)背后潛藏的古典伊斯蘭故事是每個(gè)人都耳熟能詳?shù)模贿^(guò)在今天西方化的大趨勢(shì)下,很少有人記得他們了。我的小說(shuō)是想對(duì)這些被遺忘的故事和無(wú)數(shù)美輪美奐的圖畫(huà)致敬。”正是憑借著深厚的繪畫(huà)修養(yǎng),《我的名字是紅》具備了細(xì)密畫(huà)的特色。
(楊中舉:上海師范大學(xué)中文系 郵編:20023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