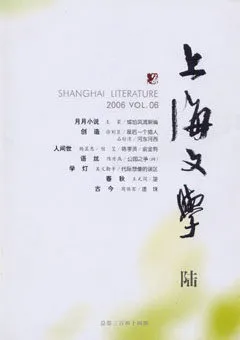大學時代
一
我的大學時代從1955年9月份開始,到1960年8月份結束。那時候復旦大學和北京大學實行的是五年制,而不是現在的四年制。高考時間是7月初,考點在南京工學院,我們這些外地考生就住在學校體育館的一座樓上面。兩天內考了語文、政治、地理、歷史四門課。我地理考得不理想,有兩道大題目沒有全做出來,大概只得了五十分左右,但其他三門功課我估計都在八十分以上,達到了復旦大學中文系的錄取分數線。我是在8月中旬接到錄取通知書的。那時候,我們老家還不通郵,信要寄到句容的一個布店里轉發。有一天父親上街去,回來后顯得特別高興,說是收到我的錄取通知書了,接著就把錄取通知書拿給我看。復旦大學的通知書是十六開的兩頁紙,白紙紅字,顯得喜氣洋洋,里面有一些熱情洋溢的歡迎新生入學的話。當時外祖父正生著重病,母親去探望他,他還問起我高考的情況,母親說我自己說:“考得還可以,應該可以上大學。”外祖父聽了也很欣慰,可惜不久他就去世了。我在8月30日開學的前一天,從鎮江坐火車到上海。第一次出遠門,我的心情既緊張又興奮,充滿了對未來生活的憧憬。
到上海時已經是凌晨三點鐘,復旦大學在火車站設有接站點,但當時時間尚早,學校的汽車還沒有來。我有點等不及了,天一亮就和另外一個法律系的學生合坐一輛腳踏三輪車到復旦。校園里綠樹環繞,十分美麗。我們住在新建的四幢三層樓的樓房里,叫第十宿舍,其中有一幢是女生樓。
進了復旦大學以后,我感覺開始了一種嶄新的生活,環境與以前是截然不同了。在歡迎新生的大會上,胖乎乎的系主任郭紹虞先生講話,他是蘇州人,一口吳方言,其中有一句話是:“我們大家(是)伙計。”給我留下深刻的印象。第一學期開的課程有中國古代文學史、文藝理論、中國人民口頭創作、馬列基礎等。教我們古代文學的老師是蔣天樞,蔣先生從《尚書·盤庚》講起,而后《詩經》、《楚辭》,一直講到漢代文學。蔣先生講課很有特點,常常有自己獨特的見解。他認為《詩經》中不存在一首愛情詩;《楚辭》則是百分之百的現實主義,沒有浪漫主義。當時現實主義是正統,在他的思想中浪漫主義可能是不好的東西,相當于“羅曼蒂克”。蔣孔陽先生給我們上文藝理論課,他上課的風格是一個課題接著一個課題地講,比如什么是文學的本質?什么是文學的階級性、人民性、黨性等等。他上課有很詳細的講稿,下面的學生要不停地記筆記。中國人民口頭創作課的老師是趙景深,趙先生知識淵博、涉獵廣泛,年輕時搞過創作。他上課時沒有講義,只有一個小筆記本,在講臺上面邊講邊唱,趣味盎然。第一學期考試我考得不太好,中國人民口頭創作和馬列基礎只得了四分。整個大學五年的學習中,我只有第一學期得了兩個四分,以后的成績都是五分。當時正在搞“反胡風”運動,賈植芳已經被捕入獄了,所以我們沒有機會聆聽他的講課。
1956年春天,全國提出“向科學進軍”的口號,學校的學習氛圍還是很濃的,大家都埋頭認真讀書。復旦大學校友曾華鵬、范伯群1957年在《人民文學》上發表了三四萬字的《郁達夫論》,在學術界引起轟動。我當時還很羨慕,希望有一天自己也能在全國知名刊物上發表文章,后來我果然也和他們一樣,成了一名研究現代文學的學者。除了課堂聽講外,我的業余時間幾乎全部用在閱讀文學作品上了。我很喜歡法國和俄國的批判現實主義小說,巴爾扎克、屠格涅夫是我最喜歡的兩個作家。當時翻譯過來的屠格涅夫作品有十幾種,我幾乎全部讀過了。屠格涅夫作品中那種淡淡的憂郁氣息和文筆的優美細膩深深打動了我。除了莎士比亞外,我對英國作家的印象不是太好,狄更斯也不例外。這可能因為我對英國文化比較隔膜,難以產生情感上的共鳴。對美國文學我還比較有興趣,讀了不少杰克·倫敦、馬克·吐溫等的小說。在大學期間,我如癡似醉地閱讀了近百部的外國小說,達到廢寢忘食的地步。那時候學生宿舍晚上十點鐘熄燈,有一次熄燈前,我看《茶花女》還沒有看完,就躲到廁所里,在昏暗的燈光下一口氣把它讀完。中國現代文學名著,我也一一找來閱讀,尤其喜歡詩歌作品,讀了不少徐志摩、聞一多、戴望舒等的詩。自己還買了很多詩集,包括戴望舒的《望舒詩稿》、艾青的《火把》等。后來我研究現代文學就是從研究詩歌人手的。
現在想想有點遺憾,我大學時的業余時間大多用來讀書了,其他活動如交誼舞都沒有學,是個標準的“舞盲”。當時國際飯店是上海的標志性建筑,如果到了上海而不看國際飯店就等于沒有到過上海,有一次我就和幾個同學過去玩。我們乘電梯一直坐到十四層,就像進了大觀園的劉姥姥,看什么都新鮮。十四層是個餐廳,女服務員過來問我們用什么餐,我們只是來長見識的,根本無意吃飯也吃不起,就笑著跑開了。那時城鄉差別還是很大的,高校里農村來的學生吃飯都不要錢,還可以領到二到四元不等的助學金。我沒有領助學金,因為我父親是小學教師,每個月可以寄八到十元錢給我,作為零用錢花已經很充裕了。那時物價也便宜,在學校里洗一次澡、看一次電影只要五分錢。當時的大學生十分單純,生活要求也特別簡單,只想著利用這個機會多讀書,把讀書當作自己的責任。
二
大學時,我曾經申請入團,但是被否決了。我對政治一向不大感興趣。同班同學張超和董達武兩個人跟我的個人關系比較好,他們鼓勵我入團,我就填寫了入團申請書。我的階級出身是沒有問題的,是地道的農民,但開入團討論會的時候,發現我在“祖母的政治態度”一欄中寫了一句俏皮話:“有吃的時候思想就通,沒有吃的時候思想就不通。”這句話引起了一些黨團員的意見,認為我的政治態度不嚴肅,大家七嘴八舌爭論起來。我自己心里是不服氣的,又年輕氣盛,就站起來爭辯說:“祖母已經六十多歲了,是個普通農民,她的政治態度如何,對我的影響并不大,對國家更沒有影響。”我一爭辯,更引起反對者的意見,認為我不謙虛,政治覺悟不高。最后表決的時候,反對票十九票,贊成票十七票,沒過半數,我也就沒有成為團員。這件事對我沒有什么影響,因為人團對于我并不是很重要。后來他們又叫我填入團申請書,當時我已經二十五歲了,也就不再想入團了。我對入團被否決的原因至今還是不服的,認為有些人喜歡抓住一點小事不放,幾乎沒有什么道理。
1957年,中央號召大鳴大放,也就是歡迎群眾提意見,助黨整風。后來又突然轉到“反右”。鳴放時我也發言了,沒有涉及到什么重大政治內容,所以后來反右時,我沒有受到牽連。而當時許多鳴放最厲害、提意見最尖銳的人都被打成“右派”。鳴放時誰具體說了什么已經記不清楚了,只有朱承樸說的“高帽子”與“大帽子”給我留下很深的印象。他對這兩個名詞有自己獨到的解釋,意思是說“高帽子”是給自己帶的,“大帽子”則是用來打擊別人的。我們班一些調干生對“反右”積極性很大,全班定了七個右派,比例還是相當高的。最高的據說是物理系,物理系畢業班共有四十個學生,定了二十個右派。整個復旦大學被打成右派的老師和學生加在一起二三百人。當時的領導似乎認為右派出得越多越好,沒有大問題,就抓住小事不放,無限上綱上線,刨根問底。因為很小的一件事或者一句話,都有可能被劃成右派,搞得人心惶惶,草木皆兵。反右運動中,我們班有兩股力量,一種是以調干生為主的黨團員干部,他們年齡比較大,社會經驗也比較豐富,積極響應黨的號召。另一種以一部分上海的高中生為主,他們出身一般比較富裕,在學習和生活上有點看不起調干生。在政治運動中,顯然調干生占優勢。全班先后有十幾個人被批,由于政策的變化,后批的幾個人就沒有“帶”上右派的“帽子”,徐達就是其中的一個。
徐達挨批的事情我記得很清楚。當時徐達、我和另外一個學語言的學生一起到校本部去上課,徐達講了一句話:“蘇聯出兵東北的時候,擄走了好多機器。”這句話被學語言的人揭發了出來,成為批判他的重要依據。徐達是上海人,工人家庭出身,學習也挺不錯。后來他的分配受到影響,被分到了貴州大學。他在那里呆了大半輩子,退休后才重新回到上海。我們至今還保持著聯系。由于政治原因而影響分配的有好幾個同學。當時我們班級最年輕、最有才華,尤其是古典文學基礎最好的一個同學,叫張瀛,因為是右派,被分到偏遠山西的一所師范專科學校,“文化大革命”時又挨整,他爬到煙囪的最高處,跳下來自盡了,是我們班同學中命運最悲慘的一個。
我們班逮捕了兩個人。其中一個叫吳宗良,因為他寫了一封恐嚇信給班上的“山雞”與“麻子”。“山雞”、“麻子”是班上兩位同學的諢名,他們都是政治運動的積極分子。通過檢查全班同學的筆跡,查出寫恐嚇信的是吳宗良。吳宗良是無錫人,他寄過匿名信后就后悔了,站在郵筒旁邊等郵局取信的人來,要收回這封信。但郵局的人說,進了郵筒的信就不能再還給本人,所以信最后還是被寄走了。他也因此被打成右派,逮捕入獄。另外一個同學的被捕,理由更是非常不充足的。
2001年,我到上海去開會,班上的同學搞了一次聚會,有徐俊西、徐欣達、鄧逸群等。他們告訴我一件事,當初逮捕那位同學時,是班干部徐欣達跟他一起走的,他塞了一張紙條在那個同學的口袋里,意思是環境險惡,讓他多注意一點。那個同學刑滿釋放后,在一個城市轉行搞園林,還寫了一本關于園林方面的小冊子。后來徐欣達與徐達、宋秀麗夫婦去看過他,受到他的熱情招待。遞條子的事也是那個同學自己提起的。聽了這件事后,我當時有點驚訝。因為在我的印象中,徐欣達是反右積極分子,他怎么會去關心一個作為階級敵人被抓起來的右派呢?他這個人道德品質倒是很好,樂于助人,被稱作“老牛”,平時嘻嘻哈哈的,很有人緣。通過這件事,我就覺得人性都有兩面性,即使在最惡劣的環境中,也會有人性之光的閃爍。這就要求人在黑暗中也不要喪失信心。作為反右積極分子,他在緊跟政策走的同時,也有自己的良知,但當時的局勢變化太快,已經不是個人所能控制的了。“人非草木,孰能無情”,看到自己朝夕相處的同學被捕,心里總是難過和同情的,所以他會在那種危險的情況下,留條子關心自己的同學。
這又使我想起一件事情,當時復旦大學的黨委書記楊西光,思想上比較左,領導政治運動很積極,公安局逮捕賈植芳先生時,是他找賈先生談話的。賈植芳先生在回憶錄中寫到,楊西光和他談完話后,送了一包中華牌香煙給他,在當時的情況下能做出這種舉動,還是很讓人感動的。這說明人性的兩面性,也說明在當時的一系列政治運動中,作為政策執行人的一方,他們也是有自己的一些看法和疑慮的。
在復旦大學的反右派斗爭中,最讓我不解的是擔任學校教務長兼新聞系主任的“老新聞”王中同志也被打成右派。他是老革命,當過山東《大眾日報》的社長。他在給全校同學做報告時,往往談笑風生,特別叫座。記得在1956年的一次報告中,他說:“什么是專家?專家就是專門家,也就是只懂一門,其他什么都不懂的人。”話說得淺近直白,道理的正確性卻顯而易見。復旦的反右派斗爭是楊西光同志掌握的,不知道為什么他能溫情脈脈地對待即將被捕的賈植芳先生,卻未能保護王中同志這樣的老革命。一個大學的黨委書記要想保護個把人還是可以做到的。南京大學黨委就未像其他高校那樣將不少老革命、名教授打成右派。前幾天與周勛初先生聊起往事,他說這與時任江蘇省委第一書記的江渭清一向溫和的政策有關。
反右運動中,尤其是通過徐達因為一句話就被批斗的事情,我得出一條教訓,那就是說話不能太隨便,在公開場合盡量少說話。比如對于農村餓死人的事,我就只跟最好的朋友講過。同學羅正堅從鄉下回來后還向組織匯報這件事,匯報材料被放在檔案里,直到1978年調動時才銷毀。當時像他這樣老實的人是不多見的,這件事也影響了他的小半生。當時班上同學分為兩派,我不屬于任何一派,跟兩派關系都還過得去。開會時,我總是一言不發,沒有批判過任何人。因為我內心對這種批判方式是不滿的。當時我并沒有政治運動的經驗,還不知道“引蛇出洞”這句話,但通過各種現象,隱隱地能感覺出來。那年放假回家,我就告訴父親鳴放時千萬不能講話,講錯了話,就要挨整。我父親和叔父是小學教師,他們在鳴放時就沒有多說,而那些鳴放得厲害的老師,很多被打成右派。我父親的性格比較謹慎,即使我不告訴他,我想他可能也不會多說什么的。
據官方統計,“反右”運動中全國被打成右派的有五十多萬人。而當時全國的知識分子是六百萬人,也就是說知識分子中十個人中就有一個人被打成右派。
三
1958年,毛澤東提出“除四害”的號召,即消滅麻雀、蒼蠅、蚊子、老鼠“四害”。有一天晚上,我們班所有的同學坐卡車到近郊寶山縣去打麻雀。麥田里到處是人,敲鑼打鼓,眾聲喧嘩,嚇得麻雀滿天飛,飛得沒勁了就掉了下來。麻雀是吃蟲子的,麻雀沒有了,蟲子就會多了,破壞了生態平衡。蒼蠅、蚊子多是不講衛生的表現,環境干凈了,蒼蠅、蚊子自然少了。光靠打,這些生物怎么能打完呢?當時的人就這么天真和主觀主義,領袖的一句話就可以導致全國性的轟轟烈烈的運動。復旦大學的校報上還登了著名科學家蘇步青打麻雀的照片。打蚊子、蒼蠅就更有意思了,復旦大學附近就是農村,每天吃過晚飯后,我們就把臉盆用肥皂涂一下,散步時帶到農民家里去,左右揮舞幾下,把臉盆上粘的蚊子數目報上去,實際上怎么能夠數清楚呢?
當時還號召大煉鋼鐵,同學們到處收集破銅爛鐵。有兩個學生到附近的工廠,把人家有油的油桶滾過來,幾個工人怒氣沖沖地找上門來,又把油桶滾回去了。還有同學把單位的大鐵門給卸了下來,什么希奇古怪的事都發生過,最后也沒有煉出什么鋼鐵來。學校還掀起過搞“超聲波”高潮,讓我們文科同學去校辦工廠鋸銅管,連續干了兩三個晚上,覺都沒有睡,最后也是什么都沒有搞出來。秋天時還要去“深翻”,掘地足有二尺深。我是農村出身的,知道深翻是有限度的,翻得太深,把下面沒有營養的黃土翻上來,上面的肥土翻掉了,莊稼反而長不好。我們班同學全部下鄉去了,翻完地后,再把肥料鋪上去,鋪了厚厚的一層。深翻后,我們學校的幾畝地草都長瘋了,莊稼卻顆粒無收。這種違反科學規律的蠢事,我們那時候做得很多。當時“浮夸風”盛行,報紙上都講一畝地產一萬斤糧食,還請了許多著名科學家來證明,老百姓不信也得信。
1959年放暑假回家的時候,家里燒飯的鍋全部拿去煉鋼鐵了。家家不起煙火,都去吃食堂。每人一天只有“三兩三”稻谷,根本吃不飽。家里留了三斤左右糯米,灶上燒不了,只好在閣樓上用砂鍋煮。煮好后,我和父親以及我的小孩,圍著鍋一起吃那香噴噴的糯米飯的情景,至今還記憶猶新。歲月雖然是艱苦的,親情卻永遠是溫馨的。
四
1958年下半年,全國開始大搞科研,以批判開路,也就是“拔白旗”。我們學校先是批判劉大杰的《中國文學發展史》,我就是在批判劉大杰的大會上見過他兩三次。同時被批判的還有蔣孔陽,把他們當作“白旗”來拔。拔完白旗后就要搞科研了。這時候我參加編寫《中國現代文學史》上冊,請以群、孔羅蓀等來指導。從他們的言辭中,我聽出以群對學生的科研能力是不以為然的,但我們青年學生當時頭腦發熱,充滿熱情和積極性,還認為他頭腦保守。上冊是內部發行的,下冊也是學校自己印刷的。我在修改聞一多這一部分時,對原稿很不滿意,自己花了一周的時間查資料,重寫了一篇近三千字的稿子。審稿的是潘旭瀾,他看了我的稿子后很欣賞,說了四個字:“簡明扼要。”后來我確定研究現代文學的方向,跟這句話有很大的關系。可見老師的一句話有時候會影響學生的一生。潘旭瀾當時是復旦大學的年輕老師,只比我大兩歲,就住在學校里,跟周斌武先生住一個房間,我一兩個月去他那里一次,跟他海闊天空地聊一陣子天,從中收益頗多。潘先生高個子,人卻很瘦,很有才氣,他的《藝術斷想》、《太平雜說》寫得很好。對于潘先生,我是很尊重的,每次到上海去都會去看望他。
上海文藝出版社的周天、余任凱等來審稿,他們跟我們這些編寫的人經常在一起聊天、打羽毛球什么的。周天、沈鵬年還和我、黃維鈞一起到唐搜家去過一趟,向他請教問題。當晚又到瞿光熙家查資料。1959年暑假前成果出來了,每個人還分到四十元的稿費,我用這筆錢的一部分買了一雙皮鞋。大搞科研的成果一般是沒有什么學術價值的,但提倡學生搞科研還是有好處的。北京大學1955級后來出了很多人才,謝冕、張炯、王水照、黃修己、陸儉明等,這跟學生大搞科研,集體編書、寫書還是有一定關系的,因為這些活動給他們提供了一個充分鍛煉和發揮自己才能的平臺。后來我們又對《中國現代文學史》進行修改,成立了一個五人小組,包括徐俊西、黃維鈞、鄧逸群、陳駿濤和我。因為參加五人編寫小組,使我得以從一茬接一茬的政治活動中解脫出來,專心讀了很多書,奠定了以后搞現代文學研究的基礎。對當初編寫組游離于政治活動之外,有些同學也是不滿的,但是因為我們也是響應黨的號召,他們也就沒有話講了。
1960年畢業前夕,每個同學都面臨著一個工作分配的問題。我們班的分配方案很晚才下來。分配志愿可以填三個,第一個一般填服從分配,我第二個填的是吉林,記得全年級只有一個到吉林的名額。公布方案之前,徐俊西約我去散步。他告訴我,我可能會到北京去,又說社會科學院文學研究所的鄧紹基來挑選人了,我就知道我被分到文學研究所了。這和我當時參加編寫《中國現代文學史》很有關系,而且我的學習成績一直優良。當時到南京也有三個名額,南京離我的老家句容最近,我又是結了婚、有了孩子的人,但我沒有申請去南京。文學研究所是全國文學研究的最高機構,能夠分到那里,我心里實在是很高興的。8月29日宣布分配方案,當天晚上我就離開了上海這座留下我永久青春記憶的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