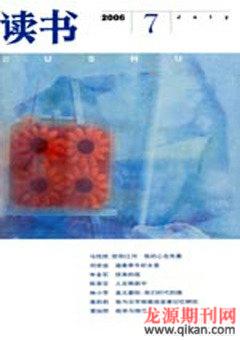問題隱含了時代的脈動
韋 兵
王東杰先生的新著《國家與學(xué)術(shù)的地方互動——四川大學(xué)國立化進程(一九二五——一九三九)》研究的是二十世紀(jì)二三十年代“國家統(tǒng)一”運動中四川大學(xué)的國立化進程。
這樣的一個內(nèi)容,入手之方是可以多樣的:它既可以從教育學(xué)視角看國家推行的標(biāo)準(zhǔn)化、統(tǒng)一化政策對高等教育的影響,也可以從鄉(xiāng)邦掌故的地方角度鉤沉許多前賢往事,以供茶余飯后的談資,當(dāng)然,最簡單的做法是,像諸多學(xué)校中都設(shè)立的校史辦一樣,寫一部“光宗耀祖”式的“地方志”。但作者還是選擇了一個歷史學(xué)者的立場。他把四川大學(xué)視為一個充滿了各種歷史變數(shù)的“場域”,并不滿足于單向和靜態(tài)的結(jié)構(gòu)分析,而是在其中發(fā)現(xiàn)了“國家統(tǒng)一”運動在不同社會層面呈現(xiàn)的地域性和復(fù)雜性。
同一個題目而有不同的書寫方式,是由于書寫者各自所預(yù)設(shè)的觀念和要解決的問題不同。如不避“簡單化”之嫌,我們不妨說:問題決定方法。年鑒學(xué)派歷史學(xué)家費弗爾曾說:“提出一個問題,確切地說來乃是所有史學(xué)研究的開端和終結(jié)。沒有問題,便沒有史學(xué)。”歷史研究很大程度上是以問題為導(dǎo)向的,問題決定了我們的研究視野和研究方法,新視野的拓展和新方法的采用多半是因為提出了新的問題。
通常認為,選擇一塊學(xué)術(shù)“處女地”就保證了成果的新穎性。然而,少有人研究的領(lǐng)域并不一定就是學(xué)者發(fā)現(xiàn)新問題的保證,沒有提供新的問題資源,在史學(xué)研究中就不能叫創(chuàng)新。就這本著作來說,事實上,一個偏于西南一隅的大學(xué),本身就是一個細碎而邊緣的話題。如果只能就事論事,僅僅做一番材料的爬梳,則至多是在浩如煙海的文字中又增加一份等待塵封的史料。
一個歷史學(xué)家在面對浩如煙海的材料時應(yīng)該認識到,研究過程其實也是一個危機四伏的過程,因為他關(guān)注的是一個他所從未曾置身其中的世界,所謂史料也原本是抱有不同目標(biāo)、不同觀念的人的“陳述”,偏見與誤讀如影隨形,伴隨著研究過程的始終。歷史學(xué)家既可能迷失在材料的迷宮中,茫然不知所措;也可能誤入意識形態(tài)、觀念預(yù)設(shè)、邏輯悖論、個人好惡的歧途,看似滿載而歸,其實一無所獲。前輩學(xué)人在談到研究者與材料的關(guān)系時使用了一個驚心動魄的詞:搏斗。所以,要從材料的海洋中捕獲一條大魚,首先要求研究者特具眼光,才能選擇一個“出人意表”的研究視角,提出新的問題。本書的意義正在于此。作者把四川大學(xué)的“國立化”進程看作民國時期“國家統(tǒng)一”運動中的個案,考察了中央、地方、民眾對此有何不同的理解,中央的政策在具體執(zhí)行中怎樣被地方性知識所改造,各利益集團又如何捭闔縱橫,運作權(quán)力。換言之,他關(guān)注的是一個“教育”運動在不同的社會層面是如何展開的。
“國家統(tǒng)一”運動是指二十世紀(jì)二三十年代民國政府加強中央集權(quán),把中央權(quán)力向地方推進的運動。從宏觀的層面上看,這場運動包括了一系列的政治經(jīng)濟改革、制度變遷和戰(zhàn)爭。按照慣常的思路,把這些大事件抓住就算把當(dāng)時的社會整體結(jié)構(gòu)演進弄清楚了,最多不過加上幾個地方的例子以做說明。這種取向關(guān)注宏大事件,注重整體結(jié)構(gòu),然而,這種思路也常常因此而忽視了政策具體落實的復(fù)雜情況。事實上,一項政策的制定者和執(zhí)行人是站在不同的價值層面和利益著眼點上看問題的,這種差距勢必在具體操作中產(chǎn)生矛盾、碰撞,地域差異尤使其變得復(fù)雜而意味深長。鄧小南教授最近提倡研究“活的制度史”。制度推行的地方經(jīng)驗便是“活的制度史”的一個方面。
任以都教授曾在《劍橋中華民國史》中指出,中央將川大國立化理解為國家復(fù)興的一個方面,而且把國立化視為中央權(quán)力在內(nèi)地擴張的標(biāo)志。但在大學(xué)這個場域中,各種權(quán)力與利益集團紛紛表達他們的立場,都要提出他們的權(quán)利訴求。中央雖然是政策的制定者,但具體執(zhí)行是由地方落實的,故其結(jié)果必然要帶上地方利益的烙印。中央政策的執(zhí)行往往要經(jīng)過地方政府、利益集團幾道篩子篩過,可能與當(dāng)初的預(yù)想差距較大。“國立化”雖有教育部指令,在地方上的運作卻擁有多層涵義。一九三一年國立化伊始,成都大學(xué)、成都高師、公立川大三校合并成立國立四川大學(xué)。劉文輝以強力合并三校是他一統(tǒng)全川的抱負在教育上的表現(xiàn),同時借以消除另一派勢力劉湘控制的成都大學(xué)。正如作者所說,無論劉湘還是劉文輝,地方軍閥對國立大學(xué)的興趣,與國家作為一種象征性資源的性質(zhì)是分不開的,控制國立大學(xué)是顯示成為中央權(quán)利的合法代表,在政治競爭中就可以挾天子以令諸侯,取得支配權(quán)。而且,擁有這個“國立”的象征性資本和消除競爭對手的象征性資源,都是宣稱政治上控制四川能力的一種方式。同時,川大為了維護自身權(quán)益,抵抗地方勢力的控制和侵害,也常常打國立這一張牌,比如在校產(chǎn)危機、經(jīng)費問題上,國立的地位多少可以提供法律上的庇護。
地方很巧妙地運用“中央”這個象征性資源來爭取自己的利益,中央的政策執(zhí)行也有韌性,常借助地方精英的影響力來推動政策的執(zhí)行。劉湘圍剿紅軍失利,一九三五年一月,由賀國光率領(lǐng)的軍事委員會委員長南昌行營參謀團入川,五月,蔣介石蒞蓉,并在川大發(fā)表講話。“地方中央化”推進到四川,四川半獨立的狀態(tài)被打破,四川大學(xué)的國立化也被視為中央化的一個部分,由此國立化進入實際操作階段。對“國立化”的解讀卻并不相同:校長任鴻雋、張頤等所理解和積極推動的國立化,與國民政府在川推行的中央化、黨化頗有不同之處;川大人認為國立以后經(jīng)費有保障,有利于學(xué)校發(fā)展,更重要的是可以擺脫軍閥控制干涉,結(jié)果隨著國立化而來的黨化使川大人捍衛(wèi)大學(xué)獨立的目的較之地方政府時代更難辦到。這種吊詭的結(jié)果是積極爭取國立化的川大人所始料未及的。以前,“中央”常被川大人當(dāng)作與地方軍閥沖突時的庇護性力量來求助,隨著國立化的深入,川大人沖突的對象換成了“中央”。一九三八年,陳立夫任教育部長,加強對大學(xué)的控制,與陳立夫關(guān)系很好,又屬于CC系的程天放突然被任命為川大校長,陳、程二人任前均主持黨務(wù),且程在浙江大學(xué)校長任內(nèi)就有推行“黨化教育”的名聲,此次入長川大,自然被川大人認為是政府要推行黨化教育,干涉學(xué)術(shù)自由,于是掀起“拒程運動”。川大人與校長程天放的沖突就是這種矛盾的表現(xiàn)。作為中央意志的代表,校長也要考慮以適當(dāng)?shù)姆绞絹碡瀼刂醒胍庵荆烫旆啪团c頗有影響力的地方名士向楚合作,希望借此增加與地方利益集團的溝通,減少政策執(zhí)行過程中的阻力。所以,實際的政策落實情況往往是由于各方對政策的解讀不同,而導(dǎo)致諸方勢力合作、斗爭、妥協(xié)的結(jié)果,是社會權(quán)力結(jié)構(gòu)下的權(quán)宜之計。而這種權(quán)宜之計又是權(quán)力結(jié)構(gòu)借以顯示其“明證性”(doxic evidence)并實現(xiàn)其自身再生產(chǎn)的方式。作者對這一復(fù)雜過程的揭示,確實有利于我們深入理解關(guān)于國家建構(gòu)、中央與地方關(guān)系等問題在具體社會權(quán)力結(jié)構(gòu)下的展開。
二十世紀(jì)七八十年代以來,國際史學(xué)界一直有一個“向下看”的方法轉(zhuǎn)型,這種取向更加注重基層經(jīng)驗和生活細節(jié)的“小歷史”,從細微事件和平常人物重構(gòu)歷史,讓人們更加了解歷史基層的生猛絢爛。在這個領(lǐng)域里,以往人們習(xí)以為常的宏觀尺度上的諸多概念從內(nèi)涵到外延都經(jīng)過了基層經(jīng)驗的重新認識,呈現(xiàn)出一些模糊、充滿歧義的地域性或集團性的理解,與宏觀尺度上準(zhǔn)確、清晰的標(biāo)準(zhǔn)定義差距較大。但往往是這些有時甚至有些荒唐的理解,而不是標(biāo)準(zhǔn)的定義左右了實踐中的人們的態(tài)度和行為方式。“現(xiàn)代化”、“國家化”這樣一些比較宏大的概念在基層的具體運作中同樣被不同背景和目的的人所理解、改造,這些不同的理解導(dǎo)致了實踐中的沖突和悖論。
一九三五年,作為主流知識分子中的一位上層人物,有留美背景的任鴻雋入長川大,把建校目標(biāo)定為“現(xiàn)代化”、“國立化”,希望把川大建成一所真正現(xiàn)代的和國家的大學(xué)。任鴻雋的談話中雖然常常將現(xiàn)代化放在國立化前面,但在他心目中明顯更為關(guān)注國立化(國家化)。這也是三十年代胡適、翁文灝、傅斯年等共同關(guān)注的問題,盡管具體見解不同,但對維護國家統(tǒng)一的態(tài)度卻是一致的。加之當(dāng)時日本策動“華北自治”的陰謀,主流知識分子對中央政府打破地域觀念的國家化政策也就更為認同。任鴻雋的觀念中,現(xiàn)代化、國家化就是要淡化鄉(xiāng)土意識,要做一個“中國人”而非“某省某縣人”。就四川大學(xué)而言,便是要成為一個國家的大學(xué),而不單是四川的大學(xué)。但這些觀念和實踐在三十年代四川大學(xué)這一場域中,卻常被有意無意地誤讀。當(dāng)時,南京中央政府推行四川的“地方中央化”,削奪地方軍閥的權(quán)力,地方實力派雖不敢公開反對“統(tǒng)一”,他們卻頗為懷疑所謂“中央政府”的資格,劉湘就暗示:都是“帶兵的官”,憑什么我劉湘就是軍閥,他蔣介石就不是軍閥?四川的地方實力派更傾向于認為這是中央在擴張權(quán)力。任鴻雋的國家化的觀念以及蔣介石親命校長的背景,此時實際上已使他處于權(quán)力傾軋的風(fēng)頭浪尖上,矛盾一觸即發(fā)。一九三六年三月,任鴻雋的夫人,同樣有留美背景的歷史學(xué)教授陳衡哲在《獨立評論》上發(fā)表《川行瑣記》,敘述旅川觀感,其中講到四川的一些“落后”現(xiàn)象,如鴉片泛濫、女學(xué)生做妾等。此文被川人認為是在侮辱川人,于是在川中引起軒然大波,最終竟導(dǎo)致任鴻雋去職。
本來想用現(xiàn)代化、國家化觀念來教育川人的陳衡哲反被川人認為是洋化、殖民化,是用“地方觀念”挑撥民族內(nèi)部關(guān)系。論爭的雙方都把現(xiàn)代化、國家化這種宏大概念作為自己的武器,他們使用同樣的概念卻在說明相互對立的觀點。這顯示出諸如現(xiàn)代化這類宏大概念在具體實踐中的尷尬和悖論。
在對這些概念的理解上,不同群體、地域的差距是明顯的。古爾德納根據(jù)知識分子對制度的態(tài)度和內(nèi)在、外在的不同取向把知識分子分為地方性的和世界主義的兩種類型,大致相當(dāng)于我們常講的具有國際眼光的“天下士”和更具國家關(guān)懷的“國士”(并不截然矛盾)。不過,對于中國這樣地域遼闊、歷史悠久的“大國”而言,廣泛存在的地域經(jīng)濟文化和觀念差異也是不容忽視的。在任鴻雋這樣具有明確“天下士”和“國士”自覺的知識分子看來,這種地方知識分子(任氏所謂的“鄉(xiāng)人”)乃是中國現(xiàn)代化進程中的消極因素。
然而,我們今天知道,不同類型知識分子關(guān)于世界的認知是不同的,他們都從自己的觀念邏輯出發(fā)理解他們生活的世界和他們在這個世界中的位置,而不大可能在實踐運用中去遵從一個概念的權(quán)威定義。即使是“國士”,從另一個角度看,也是以一種“地方性知識”來改造世界,以應(yīng)對實踐中的種種問題。換句話講,宏大概念經(jīng)他們改造后,常常成為強化他們固有觀念的原料,而不是相反。在任鴻雋等人與四川知識界的沖突中,我們看到“國士”與“鄉(xiāng)人”在諸如現(xiàn)代化、國家化一類概念上理解的差異及由此產(chǎn)生的沖突。加之政治場域與學(xué)術(shù)場域間的交錯,這些概念的內(nèi)涵變得更加復(fù)雜、含混,其沖突也明顯超出純觀念的范疇,而與政治相牽涉。
在方法論上,作者王東杰先生自承受到兩種當(dāng)代史學(xué)思潮的影響。一是“微觀史”。這一視角決定了王先生表現(xiàn)為一個“細節(jié)愛好者”。他從基層入手,充分利用檔案材料和當(dāng)事人的口述歷史,再現(xiàn)了“國家統(tǒng)一”運動在四川大學(xué)的展開。另一方面,事件展開過程中,人是主導(dǎo)因素,人決定了政策的執(zhí)行,研究事件的展開就必然講述人在其中的復(fù)雜行為,分析他的動機,這就離不開敘事。王先生對于“新敘述史”情有獨鐘,其因蓋在于此。進言之,這兩個方面又是密不可分的。本書中比比皆是的既生動鮮活又充滿矛盾的細節(jié),使這部學(xué)術(shù)性著作頗具可讀性,而通過對于這些細節(jié)的還原,那個特定場域的權(quán)力結(jié)構(gòu)及其對政策的影響也自動呈現(xiàn)在讀者面前了。
美國人類學(xué)家吉爾茲的“深描”(thick description)理論認為,人生活在自己所編織的意義之網(wǎng)中,微小事件也滲透了整個社會的符碼意義系統(tǒng),通過對于這個事件的解碼,就能夠達到對于整個社會的意義系統(tǒng)及支配這一編碼過程的權(quán)力結(jié)構(gòu)的理解。就此而言,四川大學(xué)的“國立化”過程就不只是一件偏于西南一隅的地方性事件,其背后必然包含了社會符碼意義系統(tǒng)的編碼和再編碼過程。
在這種微觀研究方法的觀照下,每一歷史事件都獲得了平等的研究價值,這可能就是本書作者所講的“歷史無處不在”的意義吧!我想,套用羅丹的話,這句話接下來其實要說:人們?nèi)鄙俚牟皇菤v史,而是發(fā)現(xiàn)歷史的眼睛。是的,我們這個時代擁有太多的成果與課題,卻太缺少“問題”,尤其是新問題。解決了一個問題,不過是提供了一季糧食,而提出新的問題,才是奉獻了一片豐饒的土地。用蘇力先生的話說,也就是發(fā)現(xiàn)了“新的學(xué)術(shù)增長點”。
很長一段時間內(nèi)歷史都是一門傲慢的學(xué)科,因為它幾乎從不反思自己的理論預(yù)設(shè)。但是,經(jīng)過二十世紀(jì)人文學(xué)術(shù)思想的沖擊,今天我們知道,在歷史書寫中我們認為“普適性”的東西也有一個建構(gòu)的過程,即使是“問題”也必須為它作為“問題”的“資格”而斗爭,以使它能夠活躍于人們的學(xué)術(shù)視野中。我們在學(xué)術(shù)史上不難看到不斷有一些問題退出人們的關(guān)注焦點,另外一些問題成為學(xué)界的關(guān)注重心。問題視野的中心和邊緣始終在變化,競爭激烈程度絲毫不遜于其他任何領(lǐng)域。
我之所以如此執(zhí)著于問題意識,是因為有必要反思“問題”背后的兩個層面,而它們說明了“問題”是如何產(chǎn)生和被顛覆的。在學(xué)術(shù)層面,學(xué)術(shù)史在某種程度上可以歸結(jié)為一部問題如何提出、衍生、變化的歷史,學(xué)術(shù)由于有了不斷提出的新問題取代被認為已解決的問題以及被證明不是問題的“偽問題”而取得進步,問題的新陳代謝是學(xué)術(shù)向前發(fā)展的動力,這其實也是人類知識增長的過程。在社會層面,提問題的方式中隱含了那個時代的思維方式、價值觀念甚至倫理道德。就此而言,提問題就不僅是“純學(xué)術(shù)”的事情,它關(guān)系到一個時代的觀念脈動。我們研究視野中的問題,往往既包含了時代的創(chuàng)見也同樣包含了時代的偏見,每一個時代提出的問題或多或少是從其現(xiàn)實焦慮中建構(gòu)出來的。因此,要了解當(dāng)今這個觀念轉(zhuǎn)型的時代,關(guān)注當(dāng)代人的“問題意識”無疑是一個富于啟發(fā)的視角。
在構(gòu)成王東杰先生問題的要素中,我們至少可以看到利益集團、社會分層、中央與地方等成分。這些成分在以前的研究中多少是被忽略的,社會被看作是鐵板一塊,似乎只是機械地接受上面的計劃、指令和政策,自己沒有能動性。在本書中我們看到的社會卻更多的是有機、復(fù)雜和分層的,它對政策充滿了多樣化的反應(yīng)。一方面,不同階層對同一政策有不同看法,另一方面,實踐中不同背景的行動者又具有不同的反應(yīng)策略。這些因素都增加了政策與社會之間互動的復(fù)雜性和不可預(yù)期性。
在這一問題取向的背后,我們可以看到,社會分層、利益集團這些概念已逐漸為社會所接受、承認,學(xué)者對于社會的解讀也不再用一種機械、單一的眼光。我們認識到,正如布迪厄所言,社會行動者并非是外力作用下消極的“粒子”,他們是各種文化、經(jīng)濟資本的承載者,基于他們的軌跡和他們憑借自身擁有的資本數(shù)量及資本結(jié)構(gòu)在場域中所占據(jù)的位置而具有一種積極踴躍行動的傾向——要么維持現(xiàn)有分配格局,要么顛覆它。這樣的認識使政府的政策制定,學(xué)界的研究視野中分層、復(fù)雜、充滿各種訴求的有機的社會概念正在取代單一、簡單、被動的機械的社會概念。也就是說,我們提出的問題中隱含了近二十年來社會轉(zhuǎn)型、制度變遷的信息。
客觀地講,新問題的提出不是單靠個人的聰明就能實現(xiàn)的,它的背后有整個時代思維方式、價值觀念的轉(zhuǎn)型。二十年前國內(nèi)學(xué)界不大可能以這種方式來提出問題。從這種角度看,本書作者的提問方式絕僅非是個人偏好決定的,而多少與時代觀念的脈動相關(guān)聯(lián)。在此層面上,作者其實也以他提出的問題參與了當(dāng)代思想史、學(xué)術(shù)史的建構(gòu)。
況且,王東杰先生也確實講到,四川大學(xué)“國立化”的進程不僅是歷史,至今仍在進行中。近十年內(nèi),四川大學(xué)先后合并成都科技大學(xué)和華西醫(yī)科大學(xué),成為“排名”靠前的教育部直屬院校,在某種程度上算是“國立化”帶有時代新內(nèi)涵的繼續(xù),可能也是親歷其過程的作者寫作的“今典”。這一“今典”在他的問題建構(gòu)中不會不是一種有力的塑造力量吧。
(《國家與學(xué)術(shù)的地方互動——四川大學(xué)國立化進程(一九二五——一九三九)》,王東杰著,三聯(lián)書店二○○五年一月版,18.80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