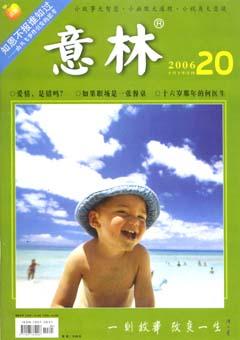哈什米安的微笑
從恨水
自從步入記者這一行,我從未幻想過自己會很出名或是弄一個“普利策獎”。然而,那天正當我愜意地坐在辦公室里盤算著十幾年后就可以退休時,老板卻把我派去了戰火重生的黎巴嫩。
“該死的!他們怕這世界安寧下來,他們就會遠離頭版頭條嗎?”我坐在吉普車里,不斷地詛咒著這又一次的戰爭。吉普車飛馳在黎巴嫩的一條公路上,司機不得不像玩模擬游戲一樣,不停地轉動方向盤來躲避公路上的彈坑。突然間,“轟”的一聲,我感到自己隨著車瞬間飛了起來!吉普車遇上了地雷,強烈的爆炸使得車身橫飛了出去!我甚至還未來得及反應發生了什么事,頭就跟隨翻滾的車身重重地撞在車頂……當我從炸掉的車門里被甩出來時,吉普車已經爆炸了!我摔在一塊干涸的田地里,除了自己劇烈的心跳外我仿佛聽不見任何聲音。我的頭有種喝過了很多烈酒后的眩暈感,竟使躺在地上的我萌生了還會繼續倒下去陷入土里的恐懼感。我下意識地抽出壓在背后的手,摸了一下頭,發現頭發已經全被血粘住了。我沒有力氣再收回手,就讓它貼在頭發上,然后閉上了眼睛……
我是在劇烈的頭痛中醒來的。當我睜開眼睛時,看到的是一個破舊房子低矮的頂部——如果那也能算房子的話。幾根歪曲的樹枝架在只殘留半截的黑墻上,上面蓋著帶有大片油污的透明塑料。我將手按在床板上,咬著牙支撐起上半身,像一個沉睡多年后又突然醒來的酒鬼一樣眨著眼。“您醒了……媽媽他醒了!”一個小男孩叫著從屋子跑出去。隨后,一位黎巴嫩婦女走了進來。她還算年輕的臉上堆積著皺紋,墩矮的身軀被一件已看不出本色的大衣裹著。她半低著頭,用平靜而謙卑的眼神望著我,好像在打量著一尊也在打量著她的雕像。“噢,您好女士……”我將腿放下床,使自己坐在床沿上,“是您救了我,對嗎?”她淡淡笑了一下,慢慢轉身出去了。那小男孩警惕地看著我,抱著一個黑色背包走到距床三米左右的地方停住了,問:“這是您的嗎?”那當然是我的背包,于是我點了點頭。“給您。”他走過來,將背包放進我懷里。我緩緩打開背包,幾乎忘了我在包里裝過什么,甚至記不清我來這里做什么!我抬起頭,望著那個小男孩,問:“你叫什么名字?”“我爸爸叫哈什米安!”他響亮地答道。“不,我是問你叫什么名字?”“我也叫哈什米安!”他的回答除了響亮還有幾分自豪。我努力笑了笑,示意他可以坐到床邊來。突然,我似乎想起了自己是為什么來這里的。“我可以為你拍張照片嗎,哈什米安?”我拿出相機,在他眼前晃了晃。“好!”他響亮地答道,隨即跳下床,跑到屋子中央站好。我迅速調整好相機,下床單膝跪在地上,將鏡頭對準他:“笑一下,哈什米安!”他似乎沒有聽懂我的話,依然面無表情地對著我。“笑一下,孩子!”我從液晶屏里望著他,大聲說。看得出他在很努力地讓自己笑,可他臉上的肌肉仍然僵硬著。我無奈地放下相機,走到他面前,蹲下說:“別這么嚴肅,親愛的小天使,看著我!”我吐著舌頭,向他做起了鬼臉。他依然沒有笑。
第二天早晨,我感到自己的情況好一些了,便下床走出了屋子。屋外是一條黃色的土路,路的兩旁排列著大大小小的簡陋房屋。有的房屋稍高級一點,因為鋪在屋頂上的不是塑料而是油氈。而有的房屋,甚至連塑料都沒有。本該空氣清新、鳥兒歡鳴的清晨,被漫天的灰土遮掩得一片死寂。我聽不到孩子們的歡笑,我看不見裊裊的炊煙,只有一個吹滿了沙土的空彈殼靜靜地躺在我的腳邊。如果此刻是在我的祖國,路上會有背著書包、三三兩兩歡快地趕去學校的學生;會有拿著“麥當勞”漢堡、一臉幸福的兒童。可是這里,在我的身邊,什么都沒有。惟一有的,只是被槍炮聲取代的寂靜的清晨。一只鳥兒——我分不清是什么鳥,哀叫著飛過我頭上昏黃的天,向遠方逃去。我低下頭,轉身想走回低矮的屋子。忽然,哈什米安興奮地從旁邊的屋子跑了出來。他的臉上依然沒有表情,但是他很高興,我感覺得到!“哈什米安回來了,我的英雄,我的父親!”他在原地跳著,小手指向遠方。我順著他的手指轉頭望去,一位身穿黎巴嫩軍裝的男人出現在土路的盡頭。我想了想,飛快跑回屋子里,將相機拿了出來。“我為你爸爸拍張照吧!”我望著遠處走來的男人,彎下腰對哈什米安說。“他很嚴肅的,脾氣也大,您最好不要向他挑戰……我和媽媽都怕他,但是他經常回來看我們。”哈什米安說著,隨即飛快地向那男人跑去。不一會兒,兩位哈什米安終于碰在了一起。父親只是摸了摸他的頭,并未有過多的親昵動作,也沒有笑容。但這些,足以讓小哈什米安滿足了!父子倆由遠及近,從我面前走過,走進了屋子里。我站在外面,猶豫著是不是該用相機去打擾一下他們這難得的相聚。
十分鐘后,哈什米安父子走了出來。看得出,這次短暫的相聚已經結束了。小哈什米安與母親站在原地,依依不舍地看著一臉冷漠的哈什米安轉身離去。我想我不能再等了,我鼓起勇氣追上去,對這位黎巴嫩士兵說:“哈什米安先生,我是中國一家報社的記者,我可以為您和您兒子拍張照片嗎?”他用警惕的目光盯著我,手漸漸伸向背后的槍。我不安地僵站在他面前,頭上滑下一滴冷汗。“好的。”他的手抓住槍,將它拿下來放在地上。我如釋重負地吐出一口氣,立刻向小哈什米安招手,叫他過來。他用難以置信的眼神望著我,慢慢地走了過來。我將鏡頭對準他們,示意讓他們靠得緊一些。突然,一身軍裝的哈什米安猛地蹲下,將小哈什米安抱進了懷里,笑了。他們父子倆同時露出了難得的笑容!這是屬于黎巴嫩人民的、久違的笑容!我迅速地按下快門,將昏黃的天空、破舊的房子、地上的彈殼和哈什米安父子的微笑,統統記錄在了我的相機里。我興奮得幾乎是手舞足蹈地跑進屋子,將相機小心地放進背包里。猛然間,一聲巨響從外面傳來!屋子劇烈地搖晃了幾下,破舊的屋頂整個被掀飛了!我摔坐在地上,突然意識到發生了什么事,趕忙爬起來沖出了屋子。在我的眼前,沒有哈什米安父子,沒有哈什米安夫人,沒有那幸福的微笑,只有幾個深深的炮彈坑……遠處的槍炮聲又響了起來。我捂住了耳朵,但這次沒有逃,而是呆呆地站在原地……
回國后的一天,我憑窗遠眺,忽然想起了羅伯特·卡帕的一句名言:
“如果你的照片拍得不夠好,那是因為你靠得還不夠近。”
(趙子摘自《青年故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