愛因斯坦與中國政治等
雷 頤等
20世紀20年代初,中國知識界對“新知”有著如饑似渴的追求,羅素、杜威等都曾應邀到華演講。對愛因斯坦,中國知識界自然也是無比欽佩,蔡元培等人曾力促其訪華,但終因中國國內局面混亂而未能實現,他僅在1922年末從歐洲乘輪船訪問日本時往返路過上海停留了兩三天。他絕不會想到,半個世紀后,自己竟會成為中國政治斗爭的一個“題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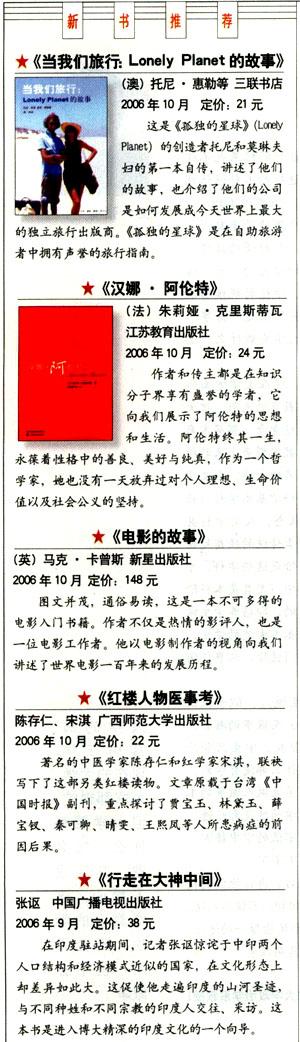
從1917年中國開始介紹其學說與思想,到1949年中國巨變的這三十余年間,他在中國的形象無疑是“正面”的。但從50年代初起,愛因斯坦的形象陡然由“正”變“負”,愛氏的學說在主流媒體受到“唯心主義”“主觀主義”“相對主義”的批判。甚至他在二戰時為戰勝法西斯而提出的要加緊制造原子彈的要求也被批判為“事實上已經為美帝國主義服務,因為在美帝國主義者手中,原子彈成了訛詐和威脅社會主義國家以及世界上其他愛好和平的國家和人民的工具”。
“文革”期間,對愛因斯坦的批判達到頂點。1968年,北京率先成立了“批判相對論學習班”,在一篇篇打倒相對論的文章中,相對論被說成是“地地道道的主觀主義和詭辯論,也就是唯心主義的相對主義”。而作為狹義相對論的兩項基本假設之一的光速不變原理被批判為是西方資產階級反動政治觀點的深刻反映,因為恒定光速意味著“資本主義社會是人類終極社會,壟斷資本主義生產力不可超越,西方科學是人類科學的極限”。他們明確說道:“圍繞相對論的爭論,已經遠遠超出了一般學術討論的范圍,始終充滿了兩種宇宙觀的搏斗,同政治斗爭的聯系極為密切。”時任“中央文革小組”組長的陳伯達,一直在“幕后”積極指點對愛因斯坦的批判,他甚至準備在北大召開萬人大會批判相對論,但因卷入林彪政治集團垮臺而未能實現。
得知北京開始批判相對論后,張春橋、姚文元即在上海組織了同樣的批判,批判“相對主義的真理觀,形而上學的宇宙論和神秘主義的方法論”。“愛因斯坦就是本世紀以來自然科學領域中最大的資產階級反動學術‘權威”“不把相對論之類的反動理論打倒,什么新科學、新技術都是建立不起來的”。
在北京、上海兩個“批愛”小組的背后,其實是林彪、陳伯達集團與江青、張春橋集團為“爭寵”的爭權奪利。
“四人幫”被粉碎幾個月后,由于愛因斯坦仍未被“正式平反”,商務印書館在出版《愛因斯坦文集》時,編輯仍心有余悸地要求譯者將譯序中稱頌他為“人類科學史和思想史上一顆明亮的巨星”刪掉,因為“馬克思主義產生以后,資產階級已經沒有思想家”了。當譯者與編輯爭執不下時,還是老科學家周培源解決了爭端:“既然思想史上的巨星,有人不同意,干脆把‘思想史和‘科學史幾個字都刪了”,改成“‘他是人類歷史上一顆明亮的巨星吧!”
1978年3月,這篇高度贊揚愛因斯坦的譯序在《人民日報》發表,標志對愛因斯坦的正式“平反”。
(作者為中國社科院近代史所研究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