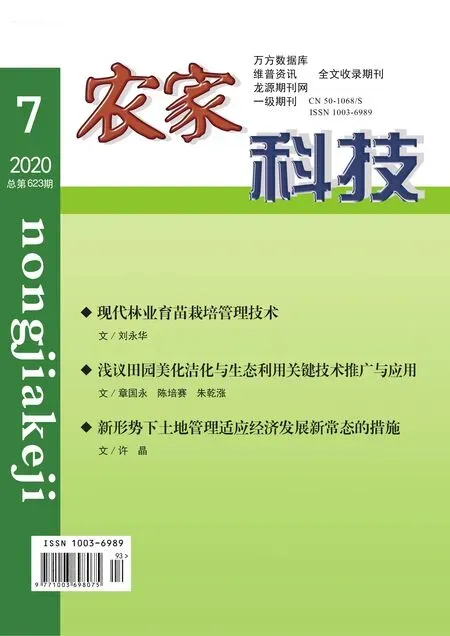現代林業育苗栽培管理技術
劉永華
(嘉祥縣自然資源和規劃局,山東 嘉祥 272400)
全球變暖和生態環境惡化問題越來越嚴重,土地荒漠化和水土流失使人們認識到環境保護的重要性,認識林業產業的重要性。林業育苗栽培是現代林業管理的重要組成部分,對林業產業的發展具有至關重要的作用。為此,應該不斷創新林業育苗栽培管理技術,為促進林業產業的可持續發展奠定基礎。
1 現代林業育苗栽培管理技術
1.1 土壤管理技術
為保證林業苗木的健康生長,應該選擇優良的土壤。為此,應該采取科學嚴格的土壤管理措施。首先,在林業育苗之前需要對土壤的酸堿度進行檢測,保證土壤的酸堿度適合林業苗木的生長。其次,檢測土壤中的營養成分。我國不同地區的土壤營養成分存在差異性,只有通過專業的檢測才能夠明確土壤中的養分情況,從而滿足預苗對土壤養分的需求。最后,在栽培之前需要進行翻土,做好整理和除草工作,為林木的健康生長奠定基礎。
1.2 種子處理技術
種子的質量直接影響著林木的成活率,在選種的過程中應該注意以下幾方面內容。首先,選擇質量好的苗木品種,淘汰不完整和質量輕的種子。其次,選種之后需要進行嚴格的消毒處理,可以通過紫外線照射或者是化學的方法對種子的病菌進行消毒,保證種子的質量。再次,對種子進行處理催熟處理,主要的方法有去蠟去油法和浸種法。其中浸種法的操作比較簡單,需要對種子進行溫水浸泡即可,讓種子能夠水分均勻。需要注意的是,如果浸泡松樹種子或者側柏種子的話,保證水溫在四五度左右。
1.3 播種方法的選擇
現階段,比較常見的播種方法有條播、散播和點播。如果種子顆粒比較小的話適合散播;如果種子顆粒中等的話是可以進行條播,條播可以采取機械化播種,提高播種的效率,保證發芽整齊。如果顆粒比較大的話可以選擇點播,必須控制好種子之間的距離,避免因為樹苗間距過小而影響樹苗的健康生長。
1.4 容器育苗技術
容器育苗技術的主要優點是能夠實現對植被分布的保護,提高樹苗的成活率。在現代育苗栽培管理中,應該突破傳統的育苗栽培器的使用,而是選擇使用現代化和易分解的容器進行育苗,其中無紡布容器技術就比較好。該技術的主要基礎材料為無紡布,該技術能夠實現對不同面部栽培的需求,選擇科學的容器育苗技術能夠提高苗木的成活率。
2 育苗期間的管理工作
2.1 苗期的管理工作
完成種子催芽之后,種子的生長到出苗需要一定的過程。應該加強對幼苗時萌發階段的管理工作,保證幼苗處于良好的環境中。首先,為幼苗的生長提供充足的水分,在播種之后結合幼苗的生長情況進行水分的補充。其次,保證苗圃內的水量,水分不能太多,不能積水,避免種子在生長的過程中出現根部腐爛的問題。最后,保證土壤的溫度適合種子的萌芽和生長,避免種子因為溫度而受到影響。
2.2 科學的水肥管理措施
有些苗木在生長的過程中需要吸收大量的水分,尤其夏季的溫度比較高,水分蒸發量大,幼苗很容易出現缺水的問題。在補充水分的過程中應該堅持少量多次的原則,盡量選擇在日落之后澆水。在澆水的同時可以加入一定量的底肥,為苗木的生長提供充足的水分和養分。
2.3 松土和除草措施
夏季雨水量過大的話,會造成土壤板結,一旦土壤出現板結問題,土壤的透氣性下降,不利于根部對養分的吸收。為此,應該定期對苗木進行松土,為苗木提供良好的生長環境。需要注意的是,良好的土壤環境也適合雜草的生長,為了保證雜草不和幼苗爭奪養分,定期對苗圃進行除草工作,為保證苗木的健康生長奠定基礎。
2.4 病蟲害的防治
在育苗的過程中可能會受到病蟲害的影響,為了不影響育苗的質量,應該高度重視病蟲害的防治工作,可以采取物理防治和化學防治相結合的原則。如在選種之后進行藥劑拌種,對或者土壤進行消毒來預防病蟲害。此外,采取科學的水肥管理措施也能夠有效的預防林業病蟲害。
3 現代林業育苗栽培管理措施
3.1 育苗理念的管理
應該重視現代化的育苗管理理念,這就需要工作人員提高對育苗的認識,改變傳統的育苗管理理念,提高育苗管理能力,通過人工育苗和機械化育苗的方式來提高效率。首先,幫助育苗管理人員樹立正確的預算管理意識,提高育苗管理人員的專業能力和水平。其次,樹立正確的工作觀念,提高育苗工作人員的積極性。具體育苗的過程中結合自身的經驗建立科學的育苗觀念,以正確的育苗觀念為指導來加強育苗的質量。
3.2 育苗技術的管理
對育苗技術統一的管理能夠提高育苗的質量,在選擇育苗技術的過程中應該應用現代技術,重視對育苗技術的創新,結合育苗實際采取有針對性的育苗栽培管理措施。此外,在具體的育苗技術管理的過程中,應該結合當地的地理環境和氣候條件下,同時選擇有針對性的預防措施,更好的發揮育苗技術的重要性。
4 結語
林業育苗栽培管理技術對林業產業的發展具有重要的作用,為此,應該在了解林業育苗栽培技術的基礎上采取科學合理的管理技術。在育苗的過程中堅持因地制宜的原則,選擇適合本地區生長的樹種,加強育苗的管理,為苗木提供良好的生長環境,促進我國林業產業的健康發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