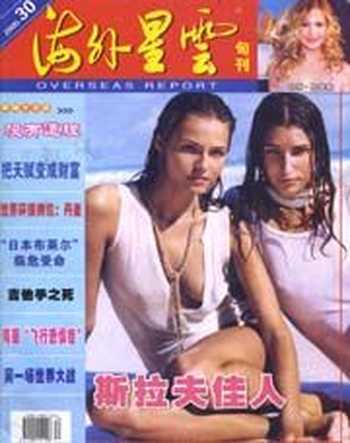反種族歧視的最前線
40年前,525名示威者在美國阿拉巴馬州的塞爾馬市聚集,要求黑人也能享有投票權。雖然遭到了催淚煙霧和軍警的阻攔,他們還是一次又一次地重新加入了游行的隊伍,并最終取得了種族平等的劃時代勝利。今天,當年的參與者們講述了他們是如何創造歷史的。
艾米莉亞#8226;博因頓#8226;羅賓遜(Amelia Boynton Robinson),93歲,從加入游行隊伍最前線的那一刻起,在30年間已經成為了為投票權積極奔走的正義之士
當我們登上帕德斯橋時,州警察在公路上站成了一排,看上去就像是一排鋼盔鐵甲的戰士。他們的頭甚至都不動一下。
約翰#8226;劉易斯(John Lewis),65歲,現美國眾議院議員,曾經擔任學生非暴力統籌委員會主席
(組織者之一)問我:“約翰,你會游泳嗎?”我說:“不會。”我們已經沒有別的路了,只能向前沖。
J.L 切斯特納(J.L Chestnut),74歲,塞爾馬市首位黑人律師
他們全副武裝,配備有催淚彈、防毒面具和像棒球棒般粗的警棍。突然,你會聽到白人說,“停,轉回去,回到你們的教堂去,法律只允許你們走到這里。這邊不允許游行。”
喬安#8226;布蘭德(Joanne Bland),51歲,塞爾馬國家投票權博物館(Selma's National Voting Rig hts Museum)的主管,參加游行的時候僅有11歲,曾因游行被逮捕過13次
突然,我聽到槍聲,有人尖叫起來。槍聲是因為有人發射了煙霧彈,但是我們當時并不知道發生了什么事情。州警揮動著手中的警棍,見人就打——男人、女人、兒童、黑人、白人——他們不在乎。人們只有憤怒和淚水。
琳達#8226;勞維利(Lynda Lowery),54歲,布蘭德的姐姐
我看見他們抓住我妹妹,把她押進了一輛車子里。我沖了過去,我以為她死了,我是姐姐,本該好好保護她。他們說她只是暈倒了,我靠在車里,不斷喊著她的名字。她終于醒了,抬起頭,看到我,尖叫起來——我被軍警打得臉上都是血。
艾米莉亞#8226;博因頓#8226;羅賓遜
我真的不明白人類怎么能這么殘忍。一位警察警告我快走開,我瞪了他一眼,他拿起警棍就打我。他再次警告我時,警棍就打在我的脊椎上,我一下子失去了意識。
J.L 切斯特納
當警察們騎馬踩過人們身上時,我竟然聽到了肋骨折斷的聲音。
約翰#8226;劉易斯
我被警棍打中腦袋,頓時暈了過去,不知道是怎么走下橋的。我醒來時躺在教堂里,已經是下午了。
J.L 切斯特納
當一切都結束后,我回到橋上,淚水不停地流下來,我對自己說,美國是無藥可救了。
這場暴力沖突導致了至少70人受傷,17人住院,并引發了80個城市的抗議浪潮——馬丁#8226;路德#8226;金發動全國各地的支持者到阿拉巴馬州集會,并在3月16日舉行了著名的塞爾馬到蒙哥馬利的游行。
格爾維#8226;金奈爾(Galway Kinnell),78歲,普利策得獎詩人
我負責在(賓夕法尼亞的)朱尼安特學院(Juniata College)教美國黑人文學,一個學生問我,“為什么我們不去呢?”
哈里特#8226;理查德森#8226;米切爾(Harriet Richardson Michel),63歲,當時是朱尼安特學院的大四學生
我們當時只是孩子,無知且感到恐懼,那真是個可怕的地方。
從蒙哥馬利白人社區的主要游行隊伍分離出來后,朱尼安特學院的學生們遭到了騎警的襲擊。
格爾維#8226;金奈爾
他們叫住了我們,把我們包圍在街上無人的角落里,哪兒也不讓我們去。
哈里特#8226;理查德森#8226;米切爾
他們拿著警棍圍著格爾維,用警棍朝他的頭上狠狠地打下去,他的頭破了,血頓時流了出來。
帕米拉#8226;克萊門森#8226;瑪康柏(Pa mela Clemson Macomber),57歲,當時只是朱尼安學院的17歲新生
警察打人時似乎還有先后順序。先對白人下手,然后是黑人,黑人婦女,白人婦女。這似乎是為了顯示他們的騎士精神。我問一位州警,“你如何向后人解釋這一切?”他無言以對。
許多在1965年參加游行的人現在仍然住在塞爾馬,離開的人也在這個有紀念意義的時刻回到了這塊他們曾經創造歷史的土地上。
喬安#8226;布蘭德
一切都改變了。在主要干道上的商店過去都屬于白人,現在那里就像是彩虹的七彩色,各色人種隨處可見。我們有黑人市長,我們不斷進步。但是許多東西仍只是表面的變化。
琳達#8226;勞維利
我回來了,這里是我的家。我參加了議會的選舉,雖然失敗了,可是我并不放棄,我打算再次參選。塞爾馬發生了很大的變化,但是這還不夠。在這兒的許多人都為塞爾馬的發展貢獻自己的力量,可是我想后輩們不一定知道他們的祖先曾經創造了這一段偉大的歷史。
約翰#8226;路易斯
當我們第一次舉行游行時,州警全都是白人。5年前(我們曾經重現當年的游行),軍警里有男人、婦女、白人、黑人還有西班牙人。當我們走到橋上時,他們歡呼起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