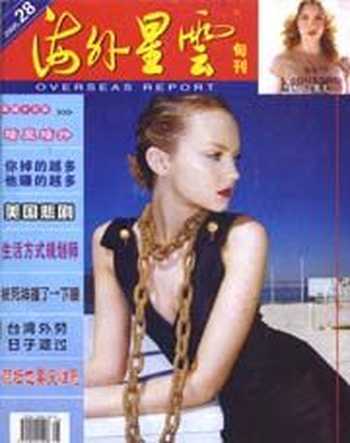他們投下了原子彈
西奧多·溫卡克,84歲,向廣島投原子彈的B-29型飛機“埃諾拉·蓋伊”號的領航員。
1944年,被認為是當時最優秀的轟炸機飛行員的保羅·蒂貝茨上校受命出任那次代號為“銀盤”的特殊任務的指揮。蒂貝茨上校決定讓我擔當領航員,他對我說:“我們要做一件事,現在還不能對你明說,一旦成功,就會結束或大大縮短這場戰爭。”我心里想:伙計,我早有耳聞。
1945年8月5日下午,長3米、直徑0.7米、重4.5噸的“小男孩”已準備就緒。當天晚上10點多鐘,我們被告知要去扔原子彈,但不清楚能否成功,也不知道會不會機毀人亡。然后,我們被安排去睡一會兒保證精力。真不明白他們怎么能指望在這種情況下我們還能睡得著!毫無睡意的我們打起了撲克牌,為的是緩和一下執行任務前的緊張氣氛。
投彈的日子定在天氣晴朗的8月6日,行動的無線電呼號為“酒渦-82”。參加轟炸的飛機共有7架,1架為原子彈載機,由大隊長蒂貝茨上校親自駕駛,他還讓士兵在機頭上寫下他母親的名字——“埃諾拉·蓋伊”。
起飛時間是凌晨2點45分,機場燈火通明。我笑著說:“這就像好萊塢的一場首映式。”從提尼安島到廣島的全程要飛很久,作為領航員的我必須使飛機保持在航線之內,準時飛抵目的地。
輕裝上陣的“埃諾拉·蓋伊”號簡直就像一根載有很多儀器和人的大金屬管。除了機尾機槍外,其他的槍械和所有的可旋轉炮塔及一切不必要的東西都被拆除。整機減輕了大約6000磅(合2700公斤)。
和往常一樣的是:在飛行過程中,有人在看書,也有人在打盹。原子彈墜下后,卸下重荷的飛機瞬間急速上升。保羅立即讓飛機轉了一個180度的彎,高度下降2000英尺(約609.6米),以最快速度飛離。一剎那間,原子彈爆炸了。我們在飛機上只看到一片耀眼的閃光。緊接著,第一道沖擊波擊中了飛機,飛機劇烈震動,尖利的斷裂聲在我們耳邊呼嘯。我們想看看轟炸后的目標變得怎樣,但根本看不清——整個廣島籠罩在黑色煙塵形成的幕布里,爆炸和沖擊波掀起了漫天的殘磚碎片,一朵巨大的白色蘑菇云直沖云霄,高達4.2萬英尺(幾近1.28萬米)。
看到這一切,你就明白:一種驚人的巨大能量釋放出來了。彼時彼刻,一個共同的想法占據了我們每一個人的心頭——正如有的人所言:“這場戰爭結束了。”你想象不出有什么人——哪怕是最極端的、軍國主義思想最頑固的、最不關心民眾的人——能夠經得起這樣一擊。
莫里斯·杰普森,83歲,“埃諾拉·蓋伊”號的飛機武器測試員。
在午夜用完早餐后,一輛卡車把我們送上了飛機。我的任務是負責檢測原子彈上的所有電子部件及需要打開的雷達等裝置。帕森斯上校則負責安裝原子彈上僅剩的幾個關鍵部件,我將工具一件件遞給他,那情形真像是在飛機上進行一次外科手術。原子彈投擲前的準備工作大約花了半小時。我的最后一項任務是爬進炸彈艙,拔下那3個小鹽瓶大小的綠色插頭。這些測試插頭將測試系統與炸彈隔開,使前者不受后者電壓的影響。我隨之換上了3個紅色的發射插頭,讓原子彈進入自控狀態。
投彈后的關鍵在于確保原子彈爆炸。從以往試投的經驗我知道,從炸彈離機到閃光或者爆炸大約有43秒鐘的間歇。我于是默數到43,卻仍不見有任何動靜,不安的感覺襲上了我的心頭。幾秒鐘過后,飛機前座的人報告看到閃光,我當即明白是自己數錯了,那個東西真的成功了。凌空俯瞰,地面升騰起巨大的云團,爆炸迅速向四方擴散,火光沖天,濃煙彌漫,此情此景讓人不能不黯然神傷,因為你知道無數生命正隨著這個城市一起灰飛煙滅。雖然任務已完成,但卻沒有人能高興得起來。
滿身疲憊的我們隨飛機降落后受到了好幾百人的歡迎,陸海空三軍將領親臨慰問。然而事實上,沒有人真正清楚我和我的隊友們究竟扮演什么樣的歷史角色。在匯報了執行任務的相關情況后,我和一同長大的好兄弟杰克·斯科特駕車去一家軍官俱樂部放松一下。正當我們在那里享受晚餐時,一位海軍軍官發問道:“伙計,告訴我們你今天干了些什么?”而我的回答是:“我想,我們今天結束了戰爭。”
弗里德里克·阿什沃思,93歲,向長崎投原子彈的B-29型飛機“博克之車”號上的武器操縱員。
8月9日凌晨大約1點半鐘時,我們奉命在“博克之車”號上集合。擔任駕駛員的查爾斯·斯威尼上校和飛行工程師進行了飛前檢測。工程師發現儲備油箱與主油箱之間的轉換泵出了故障,我們將無法利用儲備油箱中的600加侖(合2270升)燃油。但大隊長蒂貝茨上校說:“你們用不著那些汽油,這次任務沒有任何理由推遲。”
結果起飛一切正常。我坐在導航員的座艙里,有一個直徑8英寸(合20厘米)的洞口供我向外觀望,身為武器操縱員的我此次負責操縱原子彈。到了硫磺島上空的會合點時,原本應等候在那里的觀測飛機和照相飛機卻只見后者。盤旋了大約35分鐘后,我對斯威尼說:“算了,飛往第一個目標吧。”
9點5分,我們飛抵目的地小倉。不巧的是,小倉這天上空的氣象條件很差:空中布滿厚厚的云層,地面也是濃煙滾滾,能見度極低。“博克之車”在小倉上空盤旋了3周,始終未能找到瞄準點——5號軍火庫,我們只好飛向第二目標——長崎。之前有報告說長崎的天氣晴朗,但我們卻發現飛機的下方有云霧。我們在會合點時就已消耗了能維持近1小時的燃油,耗油量過大的我們面臨著成敗概率各占一半的棘手時刻。我于是建議斯威尼賭一賭我們的運氣,試著對第二目標作一次穩定水平飛行并做好使用雷達的準備,盡管這樣做違背了我們所接到的禁止在看不清目標時轟炸的命令。
我們走向雷達,正準備投彈,突然,比漢·克米特上校高喊道:“我發現了目標!”原來他注意到飛機下面的云團間有一大段空隙。于是克米特校準炸彈瞄準鏡,投出了原子彈。
投彈后“博克之車”的油料已嚴重不足,因而我們繞過蘑菇云,直接飛往沖繩島,想盡快著陸。斯威尼讓飛機作了一段很長很慢的滑翔。接近沖繩時,他無論是以內部系統呼叫還是通過閃光信號聯絡都無人回應。最后,他終于聯系上指揮塔,告之我們準備降落。飛機從跑道大約中間的位置開始著陸,直至跑道的盡頭才戛然剎止。事后,我們查看了油箱,發現僅余燃油大約35加侖(合132升),而這個數字對于一架B-29型飛機來說毫無意義——可以說我們已經沒油了。
返回提尼安島的途中我們收聽了一些當地的新聞,得知日本政府已就投降問題同瑞士政府接觸,這個消息讓我們全都興奮異常。現在回想起來,我仍認為在當時那種情況下,我們所走的是唯一可行的道路。它對于結束這場戰爭而言居功至偉,能參與其中是我的榮幸。
查爾斯·奧布里,84歲,廣島、長崎的投彈機組中一架B-29型飛機上的飛行員。
8月6日,我們飛往廣島的任務是投擲記錄原子彈爆炸之能量和放射強度的儀器。我們在蒂貝茨上校投下原子彈的瞬間掉頭返航,那一刻我見到了生平從未見過的最耀眼的光芒。駭人耳目的巨大的蘑菇云的頂端呈現出了美麗絕倫的一面,雨后彩虹中的所有色彩正不斷地從中涌現。然后飛機開始劇烈地震動起來,仿佛被什么人猛拍了好幾下。我唯一能做的事便是輕聲禱告:“上帝啊,請保護下面所有的人吧。”
在長崎,當我在觀看曾于廣島上空見過的煙塵和蘑菇云時,耳邊傳來了雷蒙德中士的驚呼:“我們的飛機要被擊中了!”看起來就像那不斷膨脹的蘑菇云要撞上我們的飛機似的。這一次,飛機受到的沖擊要比上一次強烈,我們感覺到大約3次威猛的沖擊波。
大約一周或10天之后,我和蒂貝茨駕著一架C-54型運輸機飛往長崎,隨機帶去了一些醫生和平民。人們從窗戶往外看我們,眼里充滿了仇恨,但我同時也可以看出,他們因戰爭結束而流露出的喜悅之情。我登上了一個山頂,那兒坐落著一家醫院。一個衣衫襤褸的窮人正在一旁行乞,看起來他還在流血,我為此而感到難過。在醫院里,我由墻上的一塊痕跡看出原子彈爆炸時顯然有一個人正從墻邊經過。在那之前,我確實沒想到那顆炸彈可能會造成這樣的后果。那一刻,縈繞在我心頭的只有一個念頭:我希望投擲原子彈的歷史永遠不再重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