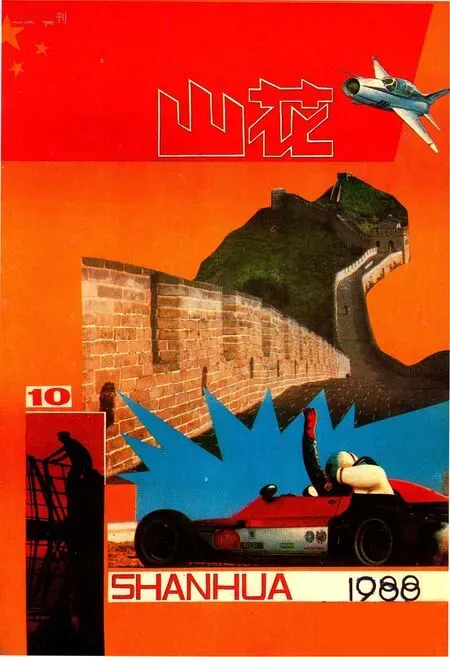積 雪
丁麗英
原來,生殖器的平面特寫很奇怪。乍一看,我還以為是一株巨大的毒蕈,拼命吸附在樹干上。仔細看,它又像沒有生命的無機物:鐘乳石,橡塑制品,或陶土的雕塑。反正失去了參照,看著不像跟人體有關。不屬于整體的一部分,可也算不上某個獨立的物件。說它是幼稚的,貪婪的,生氣勃勃的,都可以,但它的表情卻是憂郁的,憤怒的,甚至是痛苦的。
老山見我越過他的肩注視著顯屏,索興點出其它的照片給我看,并故作鎮定地問:
“怎么樣,喜歡嗎?”
“無所謂。”我說,“談不上喜歡不喜歡。”
“可你們女孩子都在為它瘋狂哪!”下了線,老山又狡黠地問,“你不覺得它很壯觀?”
“不覺得。”我說,“其實,它看上去倒像似火雞的脖子。”
“這個比喻好。很生動,可以寫進小說的。”
這期寫作班的學員,多半來自全國各地,所以都帶著筆記本電腦。不過,電腦教室的寬帶更好用,又是免費的,進來上網的人也不少。我是來幫門紅注冊郵箱的。沒想到她會找我幫忙。她跟我并不熟,只在開學典禮上見過,好像也沒怎么說話,平時更是沒機會打招呼。因為我經常逃課,偶爾去一次,也只是坐在后面,而她卻像小學生那樣,喜歡坐第一排。
“嗨,來了?”門紅笑盈盈的,朝我揮了揮手。其實,我一進教室就看見她了。在我和老山說笑時,有兩個男生插進來起哄,她卻一直縮在角落里沒有動,好像連腦袋都懶得抬一抬。
當我走過去告訴她,剛才我們在談論什么時,門紅淡淡地說,其實她早就聽見了,只是對這方面的話題,一點都不感興趣。
我不怎么相信。接著她又說:
“他們男作家真無聊。要知道,有些東西是不可以談論的,就像有些東西不可以寫進小說一樣。”
我很好奇:“為什么?不是因為害臊吧廣
“不是。”她聳了聳肩說,“可能它會破壞審美吧,反正我知道。”
我一時沒有反應過來,居高臨下地望著她。她的個頭沒我高,是中等偏下的樣子,也很瘦。鎖骨和平腕處的關節突起著,顯得怪可憐的。不過皮膚倒很白,面孔也長得小巧,骨感,是最容易上鏡頭的那種。眼窩凹進去一圈,眼睛是大了,卻白茫茫的一片,不怎么有神。
她按住長長的直發,起身往里挪,給我騰出位置。等我坐下后,她的一只手便很隨意地搭到我的肩上。頓時,我聞到了一股濃郁的香水氣味。
注冊一個新的伊妹兒很容易。我一弄完,門紅便喜形于色地說,我幫了她的忙,哪天要請我吃飯。搭在我肩上的那只手也順勢摟緊了我說,不用這么客氣的,同學嘛!她沉吟了片刻,說:“其實論年齡,我比你大了許多。”她說得不錯,我在班上年齡最小。剛開學那會兒,老山總愛跟我開玩笑,逢人便說,我是他的女兒。我覺得怪無聊的,便制止了他。
那天試好郵箱,我又指導門紅到引擎上去搜索。當她看見自己的名下跳出百來條信息時,很是驚訝,便問我,你的名字能搜出幾條?我含糊地說,大概幾萬條吧。后來想了想,又補充說,那是因為我的名字特殊,盛百合,只要和百合花有關的,都會算在我頭上。她笑了,鼻子神經質地抽了抽,很懷疑的樣子。瀏覽一番后,她又問我是不是八十年代出生的,我點了點頭。她便感嘆道:
“怪不得你對網絡這么熟。年輕真好呵!張愛玲不是說過,成名要趁早?開學典禮拍集體照那會兒,我就注意你了。那天,你穿了一件透明的吊帶超短裙。那種式樣的裙子,如今我是不敢再穿了!”
宿舍就在教室和會議室的下面兩層。底樓是男生宿舍,女生住二樓。而門紅的房間位于樓道口,第一間。從電腦教室下來,她請我進去坐坐。我猶豫著,見她打開鎖,也就跟了進去。
單人宿舍都是統一規格,家具的式樣,擺放位置,以及墻上的裝飾畫都一模一樣,連床罩和窗簾也是同一種顏色,所以我每次都會產生錯覺,以為回到了自己的房間。我習慣性地甩掉涼拖鞋,斜倚到床頭。我發現自己翹起的腳趾頭有些臟。
門紅在柜子里翻找,準備送一本她寫的書給我。這里的人都喜歡這樣,簽名送書以示友好。我本想謝絕她,卻不好意思開口。我從來沒有保存物品的習慣,尤其是書籍,看過就扔,如果上面簽了字,扔起來就麻煩了。再說,我也沒有什么好回她的。我的文章都發表在網上。
還好書都送完了,一本也找不到,門紅顯然有些失望。于是,我讓她跟我說說,她那小說到底寫了什么。愛情。她說她寫的都是愛情,絕望的愛情。還有就是,永遠不可能的親情。
那女孩長得極美,極讓人心疼,卻沒有母親。母親在她八歲的時候遺棄了她。女孩從小跟著爺爺奶奶長大。但她血管里流動著的,卻是背叛者冷酷而浪漫的血液。所以她的悲劇是與生俱來的,是遺傳的。
“果然,女孩繼承了母親風流的天性,大學沒畢業就成了未婚媽媽,而孩子的爸爸卻始終不能確定。因為她同時和許多男孩談戀愛,男孩們也對她愛得死去活來。就這樣,愛情重復著,生活也在重復。有一天她突然醒過來,發現自己早已年華老去,往事不堪回首,現實又無法繼續。孤獨的痛苦終于擒住她,將她送往等待已久的死神……”
門紅沒再講下去,因為吃飯的鈴聲響了。我回到自己的房間,拿上飯卡,然后跟她一起下了樓。飯廳在對面房子的底層,樓上是圖書館和辦公室。寫作班的生活很單調,伙食也一樣,經常是紅燒排骨,咖喱雞塊,白菜豆腐之類,和大學的時候沒什么區別。吃完飯,幾個人不是約著出去散步,就是三三兩兩地湊在一起聊天。自從宿舍的大堂里擺上了乒乓臺,就有人在那兒排隊打乒乓,看誰先贏十個球。如果下圍棋或打升級,則多半是在男生的房間里。據說班委會也重新選舉過了。但不管怎樣,人們看上去都無所事事的樣子,神情也像是在期待著什么。他們在期待什么呢?寫作?交友?更多的機遇?我不清楚。
第二天傍晚,門紅在走廊里碰見我,顯得很熱情。她穿了一套運動服,頭發高高地束在后腦勺。她說昨晚本想找我玩的,不料,飯一吃完,我就不見了蹤影。她問我躲到哪里去了?我說哪兒也沒去,我一直躺在床上看電視,后來很早就睡了。她說多睡覺可不好,這樣容易發胖。
“我就比以前胖多了,過去我還要苗條呢。”她說。
我聳了聳肩,沒說什么,我不喜歡老是談論諸如年齡、身材這類話題。接著,門紅問我愿不愿意參加女生的瑜伽小組。她告訴我,免費教大家瑜伽的,就是班上的文藝委員王靜,她以前學過芭蕾,自己在廣東還開了一間健身房。
“那她為什么還要寫作?”我問。
“可能想更好地發揮自我價值吧。”她說,“媒體是這樣宣傳她的——稿紙上的舞蹈者,你從來沒聽說過嗎?”
“沒有。”
門紅把我帶到飯廳,有幾個女生已經在那兒了。王靜老練地同我打了招呼。她穿著緊身衣,每次向下彎腰時,胃便鼓出來,乳房也不住地顫抖,感覺很滑稽。后來,她坐在軟墊上,向我們示范怎樣做冥想練習。她說,“這樣就能獲得內心的寧
靜,達到無限的精神之愛。”每天做一到二小時,門紅問我能不能堅持?我當然不能堅持了。我說,“就算每天練十分鐘,恐怕我也堅持不了。因為這種重復的動作,太單調,看著也很蠢。”
“那是為了控制能量,最終達到快樂的境界。難道你不想試試嗎?”王靜問。
“不想。”我說,“如果人一直很快樂,不是也很無聊嗎?”
這星期,我感覺時間過得快一些了。門紅幾乎每天都到我的房間來。她對我大學三年級退學的事很好奇,問我是不是因為談戀愛,還是另有原因。我不愿意說,就把話題叉了開去。還有一次,她跟我說起她的婚姻。離婚后,她一直跟女兒過。但自從女兒去讀寄宿學校,她一個人就非常孤獨。在這兒,和在家里一樣孤獨。我心不在焉地聽著,也不去打斷她。這大概就是她喜歡我的原因?當她說到,現實中的自己并非像小說寫的是個未婚媽媽時,注意地看了看我的表情。見我沒什么反應,又繼續說下去:
“他是我的大學同學,一直追求了我四年,所以我一畢業就嫁給他了。一切都合情合理,合法,女兒是結婚以后生的。”
“原來,你真有一個女兒啊!”我說。
“要不是有個女兒,我的生活完全可能是另外一個樣子。”
“什么樣子?”我問。
“不知道。也許沒這么苦吧?但也有可能早就死了。每當再也不想活下去的時候,就想到自己還有一個女兒,她不能沒有我。無論如何,要等她長大了再死。死亡被延期了。一旦死亡可以延期,產生想死的念頭,也就變成了習慣。這些年,我經常會想到死。但去死的勇氣卻越來越小。我也越來越看不起自己了,因為我同樣喪失了活下去的勇氣。”
“活下去可能并不需要勇氣。”我對她說,“活下去,只是一種習慣而已。”
昨天是星期六,阿倫一大早就來了。在我們交往的這兩年多,我也因為各種原因離開過他。他坐的是星期五晚上的那趟火車。他說,如果坐飛機,就不可能這么早見到我了。但他在火車上睡不著,一整夜都在想我。那轟隆隆的聲音弄得他很煩,以至他覺得火車會一直這樣開下去,永遠也停不了站,而他也永遠夠不著我了。我聽后似乎有些感動,但他打斷我的睡眠,仍讓我很惱火。
我們親熱一番后,我接著又睡。阿倫也睡著了。我醒來時,他還沒動靜。我端詳他。他身材修長,結實。喉結、肚臍、陰莖等部位都長得很完美,像藝術品,但似乎跟我都沒什么關系。其實,一個人完美的肉體跟他本人的關系也不大。當然,這“本人”指的是什么,我也不是很清楚。
我們坐上出租車,到他預定的賓館去。學校不準留宿,我更加有理由抱怨它了。阿倫安慰我,像煞心情特別好。我問他愿不愿意到旅游景點走一走?他不想去。他只想呆在房間里看我。我覺得有點無聊,便打開了電視。電視在放沙漠的風光片,我注視著畫面中荒涼的景色,而他注視著我。不知什么時候,他開始摟住我親吻,用熟悉的手勢撫摸我的大腿和乳房,一些敏感部位。他很投人,恨不得將整個身子都鉆進來。窗簾沒拉上,我感到秋日在我們的身體里流動,即而有一種涼爽的愛意滲透到內心深處。我很滿足。
一直到天黑,我們才走出房間,到后海的一家湘菜館吃飯。我們都很餓,再說,舌頭也需要來點新鮮的刺激。吃完飯,我們在岸上散步。天氣溫和,無風,水波不興,從游船上傳來隱約的絲竹聲,像似來到幾百年前的秦淮河:頹廢,淫糜,還有說不清楚的傷感。這時,阿倫第一次問我:你愛不愛我?我愣了一會兒才回答:總是愛的吧,不過這跟結不結婚沒有關系。他又擔心我會愛上別人。我說,誰都可能愛上別人的,這世界并不存在永恒的事物。他自言自語道,難道愛情也如此脆弱?我點了點頭,但他看不見了。黑暗中,我們誰也看不見水在流動,聽不見流水聲。我感到自己很麻木。
阿倫是第二天下午走的,我把他送到機場。我們不再討論共同的未來,似乎眼下的一切就很美好,很清晰,難以忘懷。這種幻覺讓我們暫時逃避了現實,彼此沉浸在瑣碎的關注之中。“我會想你的。”他說。他把包往上提了提,一邊做著打電話的手勢。我也朝他揮揮手。可是,當他的背影消失在候機大廳時,一種奇怪的感覺突然抓住了我——其實他非常陌生,完全是個不認識的陌生人。有一瞬間,我甚至都想不起他的面孔來了。這使我感到恐慌。不過一會兒就好了,又恢復了正
那天晚上,是我主動找的門紅。她在房間里穿得很整齊,沒開電視,窗簾卻拉上了,不知她在里面干什么。
“我在祈禱。”她說,“這樣就能夠得到上帝的恩賜,得到愛。”
她為我倒了一杯水,又說:
“不過多數情況下,我更愿意找個人聊聊。你不明白,一個人呆久了,哪怕有個人,光這樣坐著不說話,或呆在隔壁的什么地方,弄一點聲響出來,也是好的。因為祈禱往往是很難有回音的。”
當她把注意力轉到我的身上時,神情就變得開朗了,不那么憂郁,也不那么嚴肅。
“昨天我看見你的男朋友來了。”她問,“怎么樣?你們在一起開心嗎?”
“開心。可是最后,不知怎么,我突然覺得他很陌生。怎么說呢?就像從來沒在一起過。一切變得很虛幻。”
“我也有過這樣的感覺。那時我們已經一起生活了十年,按理應該非常熟悉了,可只有到最后分手的時候我才知道,他嘴巴里竟然有一顆活動的假牙,已經有些年頭了。你想,連這種事都不了解,何況其他的呢。怪不得分手后,我們形同路人。”
我笑了,因為我覺得門紅的說話方式很好笑。她經常在不該停頓的地方停頓一下,鼻子仍舊是一抽一抽的。她還有一個習慣性動作,我覺得比較色情——兩臂抱在一起,手分別探入另一只手的袖子,上下撫弄著。
門紅又告訴我,她是因為前夫的性欲太旺盛,她實在受不了,才提出離婚的。當然,那時她好像也在愛別人。她喜歡親昵的愛撫,溫柔的傾訴;其實,她喜歡的是愛情本身:那種浪漫而神秘的氣氛,那種忘乎所以的激情,而不是僅僅停留在性欲之中。她說這種三毛式的完美的愛情,這些年她一直在尋找,但顯然沒找到。她失望了,不,她絕望了。或許我會幸運一些?我不知道。我說,比起談情說愛來,我更喜歡直接的方式。
“你跟女人接過吻嗎?”她突然問。
“沒有。”
“我能吻你一下嗎?”
我沒有回答,我有點緊張。她挺直腰桿坐著,姿勢看上去很危險,臀部只觸及椅子的邊緣,而小腿懸空交叉著,上身又微微地前傾,為了保持平衡,全身像似在發抖。
“好吧。”我說,“不過快一點。”
于是,門紅走過來了。她停下,胸脯正好碰到我的嘴唇。她衣服上的香水氣味仍舊很好聞,我把臉貼近去,小心地嗅著,而她順勢抱住我的頭。吻過后,我首先笑出了聲。我很尷尬,趕緊從她的懷里掙脫出來。
接下來的幾天,門紅沒來找我,也沒去上課。可能她被自己的舉動嚇壞了,也有可能在忙別的事情。我不清楚。我安靜下來,打算寫點什么。但是,不時地,和她接吻的感覺卻總要浮上來。那種
感覺,并不如事先想的那么奇特。竟是平淡的,還略微有點苦澀。就像被骯臟的小孩吻了一下,唾液停留在口腔里,因是多余的,特別覺得乏味。可當時,門紅看上去卻很陶醉。她閉起了眼睛,呼吸還有點急促。后來我們又說了一些無關緊要的話。當我離開時,她突然看了看我,問,“難道你不想知道,我是不是同性戀?”我很想知道,但我懶得問她。
寫作班照樣是老樣子。我也是照樣吃飯,睡覺,卻什么也沒寫。時間在流逝,有時會感到焦慮,更多時候,我卻覺得這種狀態也不錯:任事物不停地在眼前發生著,開始或結束,我不去參與,也不去干涉。就像在看一部冗長的電影,除了坐在那兒,你不知道還能干什么。
今天去聽了一堂電影課。講到《法國中尉的女人》,男老師反復播放梅麗爾·斯特林普在堤壩上回眸顧盼的大特寫。那海浪之中的驚鴻一瞥,充滿了絕望和迷狂,自然地,我想到了門紅。我還想象,此刻她在干什么?和誰在一起?她赤身裸體又是怎樣的?
沒等下課,老山就發來短信了。他晚上要請出版界的朋友吃飯,想叫我作陪。我不反對,便回了信。編輯是個女的,三十來歲,很干練的樣子。和她一起還有幾個人。其中一個中年男子,介紹說是京城有名的書商,長得又矮又胖,雪人似的。編輯和書商都很無聊,老山對他們卻明顯有巴結的意思,碰了幾杯酒,就自告奮勇地說起了黃段子:
“一個傻子,在公園里看見一個男人趴在一個女人身上,覺得很興奮,就問人家,他們在干什么。人家告訴他,他們在做俯臥撐。第二天傻子又來了。同一個地方,真的有個人在做俯臥撐,傻子便走上去模仿。那人很煩,罵道:傻子,走開!傻子回答:你才傻呢!瞧你身下的人都走掉了,你還在這兒一個勁地干!”眾人笑了,說我們作家就像那個做俯臥撐的人。
這樣氣氛活躍了,眾人又紛紛說了幾段。輪到我,因為懶得講,便自罰一杯,一口氣干了。于是頭有點暈,他們后來說了什么,就沒聽進去。吃完飯,書商面露紅色。色迷迷地看著我,提議去泡吧,被我拒絕了。
再次見到門紅,是一星期之后。學校組織去香堂摘蘋果,快要出發時,她突然從樓里奔出來,跳上了中巴。她穿了一件米色的風衣,長及膝蓋的衣擺下,露出湖藍色的皮裙。她還戴了一頂式樣俏皮的鴨舌帽,墨鏡架在帽沿上。
“我不怎么喜歡集體活動的。”門紅在我身邊落座后,抬起臉,注視著我說,“不過,這樣就能和你在一起了。我挺想你的。”
我不知如何回答。門紅又問,你想不想我?我勉強道,想。不過這兩天你在于什么?她告訴我,她在寫小說。她在寫一個女人愛上另一個女人的故事。我認為這種題材很時髦,但可能不怎么容易發表。門紅說,她才不管呢!反正她要寫。要不然,心里憋得難受。過分的壓抑,會導致精神崩潰。她以前就崩潰過一次。
那時,她剛辦完離婚手續,而那個情人卻不要她了。這事她以前好像也講過,卻沒有這次講得詳細。門紅敘述起來,用的是一種嘲諷的語氣,有點得意。聲音也提高了,似乎故意要讓周圍的人聽見。她什么也不在乎。
她是突然對男人失去興趣的。她說,“你簡直想象不出,對一個真實的男人失去興趣,居然會像脫掉一件大衣這么容易,這么迅速。”
與此同時,她發現自己其實是喜歡女孩子的。那些女孩既年輕又漂亮,渾身充滿了活力。從她們身上,她重新找到了自我,找到了青春。
回來途中,門紅仍然坐我旁邊。一路顛簸,我們都昏昏欲睡,她的腦袋便自然地枕到我的肩上。我動了動,腦袋就滑下去。后半段路,她是趴在我的膝蓋上睡過來的。車箱里充滿了蘋果的清新氣味,其中還夾雜著收獲者的汗味和門紅身上的香水味。隱約中,我似乎還聞到了自己的體香,正從褲縫里滲透出來,擴散到空中,與蘋果味、香水味混合在一處。而這混合的氣味又將我們團團包圍,籠絡住,形成看不見的氣流,最后,都鉆入門紅那一張一翕的鼻孔,那里好像無底的深淵。我突然產生了一種莫名的躁動。后來有一天,我們到天壇散步,手攙著手,我好像也有類似的感覺。不過,誰又說得清,這一切不是我自己的幻覺?
宿舍里,門紅抽著煙,一邊將照片像發牌似地攤開在自己的床上。有些是摘蘋果時拍的,有些是后來在公園拍的。還有一些,則是學校的背景。照片中,我或站或坐,神情有些冷漠。我倆有幾張合影——她總是扶著我的胳膊,側立著,小鳥依人似地貼住我。也有幾張,拍的是風景——宮殿,湖,長廊,幾個老頭正悠閑地坐在那里吹笛子。
“將來,我可不想這樣,吹著笛子,等死。”門紅指著照片對我說。
我接過照片。那是在天壇,時間已近黃昏,公園里的游人漸漸少了。我記得那悠揚的笛聲,在空蕩蕩的古建筑上飄蕩,竟給人一種美妙得不可思議的印象。
“我倒是滿喜歡這種意境的。”我說。
“可這樣太漫長了。既沒有青春,也沒有激情,簡直難以忍受!”門紅把煙灰彈在保暖杯的蓋子上,“其實說心里話,我還是喜歡王朔的那句名言——過把癮,就死!”
我抬起頭,驚訝地看著她。很奇怪,這段時間她變得很多,幾乎像換了一個人。顯然她自己沒有意識到——越來越沒耐心,也越來越墮落。瑜伽早就不做了,祈禱好像也停止了,最近,她又開始抽煙,抽得很兇。食指和中指夾著香煙,其它的握緊了,托著腮。這樣,她歪著下巴的樣子便顯得有點無恥,說得好聽一點就是天真。和瑪格麗特·杜拉斯晚年拍的一張照片很像。我知道她喜歡杜拉斯,并暗暗地模仿她,可從來沒聽她公開承認過。反正我無所謂。不管他承認不承認,每個人都在變,都在重復別人。時間卻無情地流逝著。
這會兒已入冬。前兩天還下過一場雪,室內的暖氣卻打得很足,只要穿一件薄絨衫就行了。我走到窗前,把玻璃窗移開一道縫。我看見遠處的平房上還留有少量的積雪沒有融化,那就像脫了毛的烏鴉,亂七八糟地棲息在一堆,停止了飛翔。而院子里,留在樹根上的雪,有的已經變臟。那些沒有變臟的,也凝結成小塊,或不規則的小球,看上去很像泡沫塑料。踩在上面發出“咯吱咯吱”的聲音,和踩在泡沫塑料上的也差不多。楊樹光禿禿的,紋絲未動,完全是一派枯竭的景象。
“那么,你真的要走?”門紅又回到原來的話題,不過她換了一個姿勢,拇指和食指緊緊捏住過濾嘴。用力吸的時候,腮幫便會陷下去,鼻根抽搐得更厲害了。整張臉的表情幾乎是嫌惡的。
“是。我想回去了。”我說,“阿倫催得太緊,一天幾個電話。你知道,上星期他又飛來過一次。再說,這里也沒多大意思的。”
門紅直接用煙蒂點煙。我提醒她,這已經是第八根了。可她沒有理會,繼續對我刨根問底:
“那天他來,到底跟你說了什么?”
“沒什么。”我說,“他知道我跟你關系好,可能有點吃醋了。另外,他讓我……小心你。”
“小心我?是不是害怕我們相愛,甩了他?”
“差不多吧,反正他總是有危機感。你別生
氣。”
“我不生氣。可是我很想你能夠留下來。”
“這恐怕辦不到。我厭死了,我要回家。”
“留下吧。再過一個月就挨到畢業了。”
“畢業不畢業,我無所謂!要不是你在,開學一星期我就走了。”
“那么,再為我多留一星期吧。求你了。”
“不,別這樣。我最受不了自己依賴一個人了。反正我們會分手。兩個女的,你想,這是遲早的事。”
“看來你是對我生厭了。”
“我對所有人都生厭了。”
“你走了,那我怎么辦?難道只能去死嗎?”
“別開玩笑了。你不會死的。我們肯定還會再見面。”
“見面又怎么樣?反正你拋棄我了。一個被拋棄的女人只有死路—條。而你,也將永遠受到良心的譴責。”
“我無所謂。”
那天臨走,門紅要求再看看我的裸體,她想永遠地記住。說著,她捂嘴笑了。很快,她的眼睛就有些潮濕,好像剛被煙熏過,不得不瞇細著,眨個不停。
我不忍心拒絕,便同意了。
我背對著她脫了衣服,然后慢慢地轉身。我很清楚,我這二十二歲的軀體無懈可擊——皮膚光潔,毛發濃密,每個部位都勻稱,挺拔,按理說,我應該很自信的。但一想到它有朝一日也會衰老,變得丑陋,被人鄙視,卻充滿了可恥的欲望,這種自信便陡然消失了。相反,在門紅面前裸體,我總是有點心虛,每次都表現得很自卑,幾乎是羞愧難當的。
我很快又穿好了衣服。
“再見。”說著,我走向房門。我將手擱在門把上。我等了一會兒,見她沒有回答,就開了門。我記得自己一直沒有回頭。就算回頭,我也看不見她了。門已被帶上。
確切地說,門紅吞安眠藥自殺的時間就是那天夜里。可尸體是兩天后才發現的。如果她沒寫遺書,公安局肯定會懷疑到我,因為我的指紋在她的房間里到處都是,她的身上也有。不過,他們仍然把我叫去做了筆錄。對她的死,我沒什么可說的。我想盡快擺脫出來,好回家去。
“聽人說,你們倆好像那個,很要好的?”做完筆錄,警察又閃爍其詞地問。
“是又怎么樣?”
“我只是隨便問問。”
我簽了字。警察把我送到門口。他說,死者在遺囑里給我留了一樣東西。但事情沒了結之前,他還不能交給我。我想知道那是什么東西,他卻不肯說。他答應到時郵寄。
收到郵包,已經是三個月之后了。我當場打開了盒子。果然是那只女用按摩器。粉紅色的硬塑料,短柄,形棚艮逼真。內置電池。外面套了一只安全套。再外面,是一張家樂福超市的廣告紙,可能郵寄時,被人隨手拿來包裹用的。
我摸了摸,很涼,幾乎沒什么感覺,盡管它上面曾經留有門紅的體溫。我掂了掂,好像也沒什么份量。一出郵局,我便連盒一起扔進了垃圾筒。我不放心,又回頭瞄了一眼,只見廣告紙的一角還翹起著,從垃圾筒里支出來,便退后,將它掖了掖。我確定一切都遮嚴實了才離開。我迅速地穿過馬路,然后拐彎,向阿倫的汽車走去。他已經不耐煩了,在那兒不停地撳著喇叭。
此時,喇叭的聲音聽起來特別驚心,它使我想起那天深夜的電話鈴聲。可能那是門紅打的最后一個電話吧。我不清楚。也許我能救她?為此,我自責過,后來也就淡忘了。現在這個世界,誰又救得了誰呢?大三那會兒,要不是我收集的安眠藥失效,后來也不可能被人救活的。從此以后,我幾乎變成了行尸走肉。這事阿倫不知道。我不想讓他知道,一個人沒什么理由卻想尋死,聽上去確實怪嚇人的。現在輪到門紅了。當然,我也不想把這事說出去。
——之前,大概十二點半左右,門紅已經打來過電話,要求到我的房間來,和我一起睡。她說她實在睡不著,性欲難忍,她很痛苦。我沒有答應。我說,已經結束了,凡事總有個了結。她不愿意。沒多久,我就聽見她在敲我的門,在求我。聲音低低的,怕吵醒別人。好像她還哭了,可我沒有理睬她。我很厭煩。一會兒,敲門聲消失了,過了大約半個多小時,我又被電話鈴聲吵醒。我撩起話筒,只聽她的聲音斷斷續續的,很沙啞,也很乏力:
“我知道你在里面……”她哽咽道,“我知道你在里面……為什么不開門放我進去?”停了一會兒,她又啜泣道,“人,為什么都會變得這樣冷酷?!”
我一直沒有說話。后來,我就把電話掛上了。當她再打進來的時候,我沒去接。鈴聲一遍遍地響著,尖厲,刺耳,不停地在耳膜上鉆孔,我的心臟開始發痛。但我仍然沒有動。
就這樣,我睜著眼睛,躺在黑暗之中。我想象自己是一堆正在融化的積雪。后來,鈴聲便停止了。鈴聲是突然停止的。跟著降臨的,是一片滲人的死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