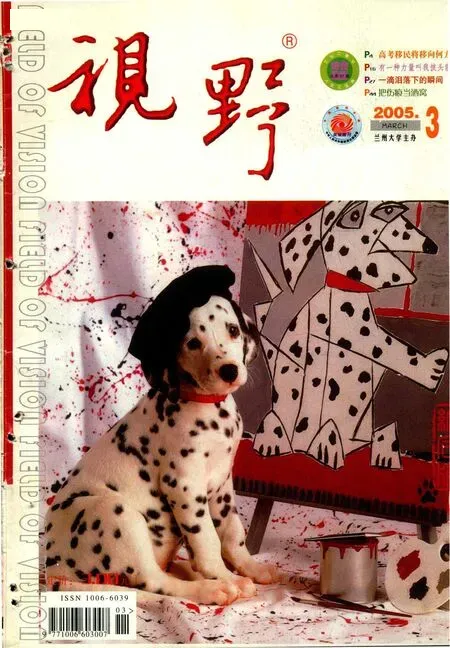有一種力量叫我披頭散發
絨 布
作為一個滿腹狐疑的家伙,我總懷疑有一種不知名的東西操縱著我,那是命運,那是神奇的力量,那是一只動不動就把你騰空拎起的毛茸茸的大爪子。公元1972年的春天,那只大爪子把我從娘胎里掏了出來,從此我就無奈地姓張了,無奈地成為北方人了,無奈地屬老鼠了,還無奈地成為可恨的金牛座人士了。要知道,我并不想要這樣的生活,在我若干年后的夢想中,我至少應該誕生于富足的90年代,做個斯文的江南人,聰明伶俐的雙子座,屬相最好是保護動物;至于姓氏,也要顯得矯矯不群——比如令狐沖撞,最起碼也得叫個司馬相公。可沒人和我商量,我也沒敢和別人商量,我怕我的老父親把我掐死。
后來的種種遭遇也證明了這一點——在這個世界上,你可以做主的事情少得可憐。作為一個天真無邪的小小的嬰兒,我被捆得像個大粽子,何時吃奶、何時換尿布都由不得我,我只能仰面朝天,眼巴巴地看著屋梁,思索著不怎么深刻的問題。等我能四處亂竄的時候,我得到的待遇更令人發指,我那浪漫主義的母親把我打扮成一個小姑娘,給我梳了一個沖天小辮,領著我招搖過市;更可怕的是,據群眾反映,在我毫不知情的情況下,我還自由進出了幾次女廁所——想想吧,這對我的靈魂是多么大的摧殘。
好不容易熬到小學一年級,我以為我終于可以自由了。上學第一天,當我們的班主任走上講臺時,按照規定,我們這些小蘿卜頭齊刷刷地站起來大喊“老師好”。不幸的事情發生了。由于我叫得比較賣力,那一嗓子令班主任龍顏大悅。老太太沖我嫣然一笑,小手一揮,“就是你了”。我不記得當時我是否哆嗦了一下——至少現在我哆嗦了一下,從那天起,我開始當上了班長,開始了漫長的從政道路。這已夠倒霉,當那群壞小子興高采烈地四處撒野的時候,我可憐巴巴地帶領一群傻丫頭打掃衛生,還要身先士卒,竄到窗臺上擦玻璃。不罵人,不打架,不考試作弊,不摔跤爬墻偷玉米,不做革命兩面派,瞧瞧,多么慘絕人寰的生活。更可悲的是,我還毫無知覺,胳膊上掛著兩道杠美得不得了——靠,不就是多了一個等于號嗎?
還不僅僅止于此。把課文抄幾遍,我得聽老師的;吃什么穿什么,我得聽咱媽的;帶多少零花錢、過年買幾串鞭炮,我得聽咱爸的;要合伙欺負哪個臭小子,我得聽咱哥的;剃光頭留平頭,我得聽理發店里的劉大爺的;先拔哪顆牙、后拔哪顆牙,我得聽李大夫的;早晨幾點起床,我得聽那個破鬧鐘的;打開收音機沒的聽,只好聽劉蘭芳的評書了。十一年啊,人這一輩子能有幾個十一年?而時光流逝,我又變成了什么樣子——表情是莊嚴的,笑容是謙遜的,說話是拐彎抹角的,走路是目不斜視的,總而言之,是中國70年代制造的,想升級換代,一時還找不到合適的零件。江湖一入深似海,從此小張是路人。悲愴。
好不容易混進了大學,以為從此就可以揚眉吐氣了。估計當年的同學都有如此的感覺,所以我們一度喜歡跟著唐朝樂隊高唱《國際歌》——起來,饑寒交迫的奴隸,起來,全世界受苦的人!滿腔的熱血已經沸騰,要為真理而斗爭!后來我們就不怎么唱了,因為我們突然明白一個道理,舊社會雖然被我們打個落花流水,可接踵而至的新社會也把我們打個落花流水。你再喜歡賴床,你也得趿拉著拖鞋排隊買稀飯吧?你再不喜歡看書,你也不能因為背不出幾句深奧的話而被人恥笑吧?你再特立獨行,在善良的老教授面前,你也總得點頭哈腰幾下吧?你意志再堅定、情操再高尚,也總得找個女朋友裝飾一下門面吧。
以后的日子估計都大同小異,每次和大學同窗們聚會,看到那些紅潤得失去了棱角的面孔,不由得悲從心來。想想吧,那些家伙曾是多么的高傲啊,他們寫出的詩歌又是多么的晦澀深沉啊。可今天,大家眨巴著眼睛,講著黃色段子,即使想感嘆一下生活,也只有抿一口小酒呻吟一句“啊,生活”,然后都沒脾氣了。
其實我的郁悶是顯而易見的。某一天我終于作了一個英明的決定,我終于無須和任何人發生關系了——我沒有家庭,沒有單位,沒有領導,沒有一切。我在別人的城市里生活,我在不屬于自己的床上睡覺,我看著別人的文字,琢磨著自己的文字。我有一個大皮箱,假如我樂意,我可以飛快地把一切包括自己都塞進去,然后隱遁在這個世界里。我最有價值的財產就是一張身份證,上面的照片還模糊不清,看起來面目可疑。原本我以為自己終于四大皆空了,后來我發現一個問題——我還是不自由的,我還有文字,我沒有勇氣把文字也甩進垃圾箱。這真令人羞愧,一不留神,自己居然成了臭名著注的文學青年了。當大學同學表揚我的執著時,我發現他們的表情六分戲謔、四分同情,我感覺我有必要配合一下——我應該擺出一個討飯的姿勢,把手掌伸出,可憐巴巴地說,大爺,我得生活,我得生活啊!
我沒有擺脫。那股神奇的力量還在,那只動不動就把我騰空拎起的毛茸茸的大爪子還在。我看著自己的文字,時常分神幻想著某些曼妙的景象——可以有飛花,可以有飄雪,可以在長河落日的背景中飲著一壺老灑,可以醉得不知歸途,可以讓自己蒸發,可以讓自己羽化成大雁溶入這一抹的暮靄……然而,這都是幻覺。我知道我們每個人都有靈魂的,假如我的靈魂可以竄出肉身,假如它可以認真地端詳我,它勢必可以看見這樣的一個影子,然后驚駭于其陌生——這就是我,歪斜地坐著,習慣性地敲打著鍵盤,摸摸鼻子,時而得意洋洋地搖晃著香煙,披頭散發,冷笑連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