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肺結核——人類死亡的行刑隊長”
董明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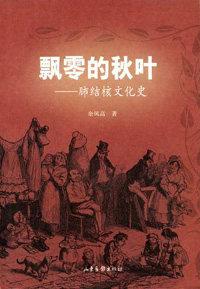
英國大詩人濟慈在1819年寫了一首詩:“年紀輕輕的,就長得臉色蒼白,瘦骨嶙峋,不久歸道山……”兩年后,他死于肺結核,終年才26歲,那首詩就是他自己的寫照。濟慈生存的年代,正是肺結核最猖獗的時代,肺結核是那時候病死原因的禍首。為此,濟慈特別為結核病取了一個綽號:“人類死亡的行刑隊長。”
肺結核真的那么厲害嗎?據(jù)資料介紹,自1882年德國科學家科赫發(fā)現(xiàn)結核菌以來,迄今因結核病死亡人數(shù)已達2億。而最新的資料表明,全世界結核病人死亡人數(shù)已由1990年的250萬增至2000年的350萬。75%的結核病死亡發(fā)生在最具生產(chǎn)力的年齡組(15~45歲),全球已有20億人受到結核病感染,每年感染率為1%,即每年有約6500萬人受到結核病感染。
值得關注的是,肺結核似乎更愿意眷顧文學藝術界的人士。除了濟慈外,跟他齊名的英國詩人雪萊、《金銀島》的作者斯蒂文森、鋼琴家蕭邦及小提琴家帕格尼尼等知名的文藝人士都得了肺結核。另外,從15世紀的模特西蒙內(nèi)塔·韋斯普奇,到20世紀20年代的作家凱瑟琳·曼斯菲爾德和30多年前的電影明星費雯·麗,這些美的寄寓者和美的創(chuàng)造者遭到這種疾病的襲擊后,像花朵一樣枯萎、凋謝,令人不勝嘆息。那個時代的藝術家為何偏偏遭遇肺結核?這是此病的得病機制和藝術家的個性特點決定的。書中對他們的特點進行了深刻的分析:這些人大多都智力聰慧,才華橫溢,而且往往多情善感,尤其是感情特別強烈且纖細,甚至到了過度敏感、過度脆弱的地步。也許正是由于這種原因的存在,肺結核才得以在他們身上更加殘酷地肆虐。
令人驚奇的是,肺結核雖是一種不良的疾病,卻又是一種悠閑逸適的疾病。因為對于俗人和暴發(fā)戶來說,肺結核正是高雅、纖細、感性豐富的標志。另外,在貴族已非權利而僅僅是一種象征的時候,肺結核病患者的面孔成了貴族面容的新模型。更有趣的是,用相當嚴謹?shù)尼t(yī)學和文學眼光來評判,肺結核具有“病態(tài)美”,非常符合浪漫情調(diào)的作者激情投射和情節(jié)安排的需要。更有甚者,拜倫說:“我真期望自己死于肺病”,而健壯、充滿活力的大仲馬則試圖假裝患有肺病。他們之所以這樣做就是因為肺結核乃是那個時代的時尚。
如果你讀過18、19世紀的小說,或在電影、電視上看過關于那個時代的故事,往往會發(fā)現(xiàn)其中的一個共同點:幾乎都有一個患“癆病”的角色——生病的孩子,竭力要完成其巨作的將死的藝術家,臥床不起無法照顧家庭的母親……他們面色蒼白,身體虛弱,經(jīng)常咳血,并慢慢地消瘦。這就是典型的肺結核癥狀描寫。由于肺結核病的這種性質(zhì),此病多數(shù)患者最終必死的歸宿,以及患病期間所形成的病態(tài)美,當然都是浪漫主義藝術家所追求的,小仲馬的《茶花女》、曹雪芹《紅樓夢》中的林黛玉,都屬此例。
疾病使人本身產(chǎn)生一種宣泄的需要,人的內(nèi)心需要撫慰、需要克服對疾病的恐懼,從心理學上講文學符合這些表達程序。文學、音樂等藝術不僅能表達人的正常心理,還能表達人的非正常心理,對人性的弱點、陰暗面,文學有著其他傳媒不可達到的特異性。這也是許多文學家、藝術家“喜歡”患上肺結核“藝術病”可理解的原因。因為只有文學、藝術,才能釋放他們。
書名“飄零的秋葉”就深刻蘊涵了此中的真正意義。自古以來,人們都把秋天看成是成熟和收獲的季節(jié),這使他們看到的是滿山的紅葉在金色的陽光掩映下,有著說不盡的美麗。可同樣是秋天,在浪漫主義作家的眼里,它的美卻并不是由于這是一個成熟和豐實的季節(jié),而是由于隨這季節(jié)而來的枯萎、飄落的秋葉。難怪德國自然科學家亞歷山大·馮·洪堡說:“古人只當自然在微笑、表示友好并對他們有用的時候,才真正發(fā)現(xiàn)自然的美。浪漫主義者則相反:他們發(fā)現(xiàn)自然在蠻荒狀態(tài)中,或者當它在他們身上引起模糊的恐怖感的時候,才是最美的。”
這或許就是肺結核所特有的非同一般的文化背景。
《飄零的秋葉——肺結核文化史》余鳳高著山東畫報出版社2004.8定價:17.50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