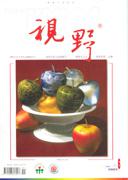一秒鐘32步
施國安
一秒鐘32步—一這不是常人所能達到的水平。擊打根本無法區分,只聽到陣陣類似蜜蜂發出的嗡嗡聲。這只蜜蜂叫邁克·弗萊利。他是當今吐界上最著名的踢踏舞王。
他的兩條腿的保險費為4000萬美元。
弗萊利可稱作是一塊跳舞的料。他創建的舞蹈團Lord of the Dance給我們帶來了新的節目一一舞蹈、艷麗的服裝、戲劇性音樂和現代煙火技術。照弗萊利先生的說法,在這個世界上我們多少都是舞者。
記者:弗萊利先生,你認為世界本身就是一種舞蹈,或者你還是把職業和生活加以區分?
弗萊利:我在舞臺上跳的時候,與其說我在從事某種工作,不如說我進入了一種非常愜意、非常合我本性的狀態,我以此為生。每次演出結束的時候,我總是很難從我的“那個”生活中擺脫出來,回到地面,回到大家認可的生活中來……事實上,現實和舞蹈還是不同的東西。對我來說,舞蹈就是我的生活,是第一位的。
記者:不過,如果嘗試一下的話,是否可以把我們的生活和某個舞蹈作比較?
弗萊利,當然可以。不過,我想說的是,生活恐怕不是一個,而是很多最不可思議的舞蹈的匯合……但是除此之外,對我們的演出還有著某種整體的感受,它能使觀眾腦海中浮現出某個整體的,以某種方式占據主導地位的舞蹈……這就是對世界的最準確的反映。華爾茲在1 9世紀某種程度上正是這樣占據統治地位的,它最準確地反映了那個時代的和諧和平穩。20世紀初出現了探戈,一種更具活力、更強烈、更具摧毀力的東西,而它也是世紀之初的準確反映。20世紀下半葉當然是搖滾,節奏開始在世界上占主導地位。現在我們大家的生活節奏快得發了瘋,主要任務就是趕、趕、趕……容我斗膽期望,我們的演出是最準確反映21世紀節奏的嘗試。
記者:知道嗎,我發現一個奇怪的東西:現在不興跳雙人舞,要不獨舞,要不一人群人在舞場上群舞……另外,如今年輕人不叫跳舞,而叫……怎么說呢……跳幾步……
弗萊利:是的,世界在變化,我們大家在變。你注意到沒有,人們現在去迪斯科舞廳不是為跳舞,是吧?舞蹈不是目的,不過是一種形式而已……人們去舞廳出于其他目的……要感覺自己是完整的,要自我表現,要充電……我不是心理學家,不打算解釋大眾跳舞的現象……但是,我能理解獨舞者。這是現代人用來表現絕對自由、完全個性化的形式。這不是和世界的對話,而是獨白,一個有關自己完全獨立的聲明:“這就是我,請接納這個原本的我。”現代藝術有個新概念“新解剖學”,其實質是:生理、遺傳和文化空間已經變化,與之適應的應該是另一種動作。我們看到的正是如此。
記者:你在某次訪淡中說過,除了自己著名的踢踏舞,其他舞你都不精通。為什么?
弗萊利:確實如此,華爾茲我就跳得很笨拙。如果我要想跳各種舞都能取得成就,我就沒法更多關注自己喜歡的。你知道,人是多才多藝的,但是在某個階段他得選擇某樣他做得更好的東西。只有成為某個專門領域的專家,一個人才會取得成就。我把踢踏舞稱作舞蹈的特殊形式,它不同于世界上任何其他舞蹈。我跳的是快速度的愛爾蘭傳統舞蹈,但同時我配合了上體和上肢動作。這是某種我用一些細節做成的東西,沒法下什么定義。換句話說,某種大雜燴……
記者:甚至著名的藝術家現在也陷入非常復雜的境地。他們被迫考慮的不是創作,而是有沒有市場,能刁;能賺錢……
弗萊利:確實,如今藝術家不僅要考慮出新作品,還得考慮怎么推出、保存自己的作品,同時還要盡力不去關注多余的東西。今天藝術家的生存形式與其說在于了解新事物,不如說是要把自己和一切不需要的東西隔開。現在的世界、現在的藝術中影響我們的荒謬東西實在太多,藝術家首先必須學會區分什么是真正的東西,什么是假冒偽劣。比如說我,已經1 5年不看電視,我根本沒有電視機。我禁止自己看電視,而且一點不為此惋惜。(羅大友摘自《世界之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