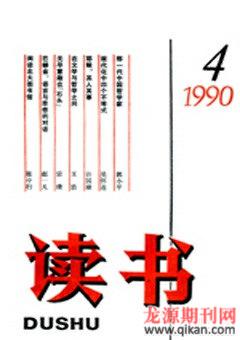古代文論的大工程
梅 君
《中國古代文論類編》可以看作古代文論的一個大工程。從體例看,編者把中國古代文論分為創作論、文源論、因革論、鑒賞論、作家論等六編。其中創作論占了一半以上的篇幅,這既符合中國古代文論的實際情況,也符合重視文藝內部規律研究的時代潮流。這六編構成了古代文論的基本框架。我以為這種類編的形式至少有兩大好處:一是可以一目了然地把握古代文論的整體格局;二是便于專題研究。特別是古代文論中有民族特色的一些范疇,像意境、趣味、文氣、風骨等,把有關的論述匯聚在一起,為深入研究提供了不少方便。
本書基本上是語錄體,沒有注釋,但在每一部分前面都有二、三千字的說明,對該部分的內容作簡要的評述,并對一些意義比較模糊的概念如文氣、風骨等進行必要的解釋和追溯其源流,這對于在古文論領域涉足未深的讀者是有幫助的。編者的觀點集中體現在對古文論的評價上。應當承認,這些評價大都是比較精當的。如在比較“言志說”、“感情說”與“性情說”時指出,“言志說”往往更多地注重思想——儒家思想,對感情的強調沒有“感情說”那樣強烈,而“感情說”光講感情忽視思想,又帶有片面性。“性情說”在理論上更完善一些。因為“性情”的內涵,不僅包括思想,還包括感情以及氣質、稟性等。這種評論對讀者是有啟發的。又如“創作論”之二的“說明”中,編者論述了有關“文與道”的問題,指出道學家用“道”排斥感情,用“道”否定“文”,是“愚妄和偏見”,“是扼殺文藝的荒謬理論”,而古文家韓愈提出的“不平則鳴”等等,不僅沒有排斥感情,還很重視文辭,則是頗有“可取之處”。這種說明就不只是對資料的簡單評價,而是有所分析批判了。又如編者引袁枚“詩者,人之性情也。其言動心,其色奪目,其味適口,其音悅耳,便是佳詩”后,指出“這種非功利的純藝術觀點,頗有點離經叛道色彩,在當時不啻空谷足音”,“就其沖破儒家的思想標準來說有一定的積極作用”,這種評價無疑是中肯的。但編者又認為古文家“主張思想性與藝術性統一而又把思想性放在第一位的,人數最多,也最有道理”。這種看法卻值得斟酌,當然,編者完全可以堅持自己的學術觀點。
(《中國古代文論類編》,林英編,海峽文藝出版社一九八八年六月第一版,<上>10.50元;<下>8.50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