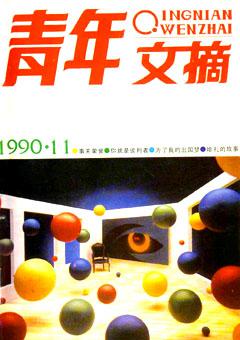第一印象有時并不可靠
鮑勃·歐·沙利
三個青年人在瑞士的赫格斯維爾上了開往盧塞恩的火車,毫無疑問,他們剛登過梯特里斯山回來。其中的一個是姑娘,穿著一件嶄新的黃T恤襯,胸前印有“Titlis,3200公尺,10,500英尺”的字樣。
他們正巧坐在過道的另一邊。那個清秀的姑娘雖然卷發亂蓬蓬的纏在腦后,卻依然嫵媚動人。兩個小伙子中間有一個跟她長得很相像,似乎是她的兄弟。
另一個小伙子從背包里掏出一副立體聲耳機,順手往頭上一戴,音量開得很大。
人們在國外旅行時,往往容易將同胞在外不拘小節的行為看成是對他人的冒犯。這時,我不由低聲祈禱起來:“我的上帝,但愿他們是英國人,德國人,或是法國人。”
那個姑娘往嘴里塞著口香糖,朝我莞爾一笑。“嗨!你說什么?”
天哪,他們也是美國人。
我忍了幾分鐘,不得不朝戴耳機的小伙子俯過身去。
“聽上去象是查比·切克爾的曲子。”我搭著話,希望他能悟出話音,把音量擰小些。
“誰?”他茫然不解地問。
姑娘搖搖頭。“不,不是,他對古典音樂沒興趣。”
又過了一刻鐘,我的妻子喬伊娜,身為專職的聽力檢測醫師,也覺得有責任說上幾句。她輕輕地拍了拍小伙子的膝蓋,他摘下耳機,不解地注視著喬伊娜。
“你要是繼續……”她剛說了個話頭,小伙子卻搖著頭朝她側過身子,表示聽不清她的話。喬伊娜提高嗓門又說:“你要是繼續那么大聲的放音樂,會損害耳蝸的。”
“你說什么?”他喊話似地問,隨手關了耳機。
“你這樣聽會損害耳鼓的。”喬伊娜的話音在突然沉靜下來的車廂里象吶喊似的。
姑娘和她兄弟聽了喬伊娜的喊叫都樂極了,戴耳機的小伙子卻點頭稱是。“你會弄壞聽覺的。”我妻子繼續規勸著。
小伙子臉上浮現出理解的神情。“有道理,”他說著“謝謝”,便把耳機摘下掛在脖子上,又將旋紐往回擰了擰。這下對他來說,音量可能是弱多了,可我們卻覺得嘈音依然如故。
“小伙子,”我招呼道,“還能旋小點嗎?”
“沒法子啦,”他說,“旋紐壞了。”
于是,我們就在“西德·維舍斯”等流行音樂的嘈雜聲中一直挨到盧塞恩。
在火車站附近,我們得乘扶手電梯,在那兒又一次碰見那三個青年人。他們正跟在一個體態臃腫,行動蹣跚的老太太后面,耐心地等她先上電梯。老太太站在電梯前一前一后緩緩地晃動著身體,顯然想等待機會,平穩地踏上一級級往上滑動的踏梯,以免跌跤。她好不容易才瞅準機會,踏了上去。
老太太剛登上電梯,站得似乎挺穩當,可沒一會就開始搖晃起來。跟在后面的三個青年一下子沒能扶穩老人,趕忙撲到滑動的梯子上抬起驚嚇不已的老人,扶著她邁到平臺上。
老人左眼上方碰破的傷處流血不止,越是用圍巾擦,血淌得越多。她不迭地謝著年輕人,為自己給他們招惹的麻煩而抱歉。令我們驚訝的是,三個青年根本沒有顧及自己,只是關注著老人的傷勢。
卷發姑娘用手捂住老人的傷口,最后又將老人的頭抵在自己的新T恤襯胸前來止血。兩個小伙子則匆匆把老人的行李集中到一塊,然后扶著她走到街上。
我和喬伊娜在一旁注視著。他們截住一輛出租車,操著生硬的德語同司機爭論著。司機不愿搭載老人,不過他用對講機替他們喊來一輛救護車。
幾分鐘后,救護車呼嘯而至。老太太認為自己一身是血,一再謝絕,不肯上車。三個年輕人則連哄帶勸,幫老人上了車,并把她的行李放在她身邊,救護員忙著關上車廂后門。
“請等一下,”老人喊著。“你們這些好心人,謝謝,好心人。”老人似乎還想說什么,可是救護員關上了門,救護車又響著鈴聲,飛馳而去。
火車站對面有一座橋,過了橋可以徑直走到盧塞恩市的一個風景區,由卵石鋪成的街道一處沿一排臺階可以直通羅斯河。以前,我和喬伊娜來此旅游,曾在那兒眺望過暮色里的天鵝。
那三個青年在我們之前到了河邊,他們正坐在臺階上,一邊說笑著,一邊在河里洗著衣物。我們在以往常坐的長登上坐了下來,旁邊有一對中年瑞士夫婦在低聲私語,那個男子看見我們便側身招呼。“我正跟我的妻子講著呢,”那個男子說:“如今的年輕人真是毫不顧忌。他們飄洋過海,竟來我們這個世界上最古老最美麗的城市的河里洗臟衣服。”
喬伊娜竭力平靜地反駁那個男子。“先生,”她莊嚴地說:“這三個青年剛才幫助了一個在電梯上摔跤的老太太。我想,他們是想在血跡凝固以前洗掉沾上的污血。”
那位瑞士婦女朝河邊望去,她的丈夫贊許地點點頭,然后裝上煙斗,夫婦倆一同站起身來。
“第一印象有時并不可靠,不是嗎?”他自嘲地說。
是的,第一印象有時并不可靠。
(胡開杰朱和平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