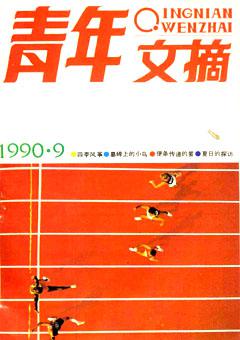女孩兒,何須界墻高高
孫 珙
女孩兒,你在母親的呢喃細語中凝思;女孩兒,你在家人的噓寒護暖中長大。你從小就接受了許多做好女孩兒的訓戒。于是,便塑造了你的低眉順眼,垂手恭上;悄聲細語,步履輕盈。悄悄的,你已步入19歲的年齡。睜著好奇的雙眼,禁不住外面世界的誘惑,心兒癢癢的,可你怨恨自己是女孩。
周未,你接到一個電話,是一位男士打來的,一位很帥的小伙子,沒準你在心里偷偷地喜歡過他。話筒里傳來純正的男中音:“小文,晚上我能榮幸地邀你跳舞嗎?”
“啊?什么?跳舞……”你心兒忐忑,語無倫次,手心浸著汗。
“你答應了?”仍然溫和如故。
“我,我不會跳的……”你不知如何做答。
“沒關系,8點在“白天鵝,門口見好嗎?”
你呆呆地拿著那已無聲響的話筒,一絲惆悵黯淡了你少女的明眸。于是,整整一個下午,你迷亂在猶疑之中。你自問:他為什么偏要請你呢?你是不是應允得太輕率了呢?假如這次答應了以后他會不會……一連串的疑問碰撞著你的小腦瓜,一個下午你沒有笑容,還是母親的教誨“拯救”了你:“女孩兒,不能輕易答應男子的邀請。”
雖然你很想去跳舞,最終不得不悻悻地踏上回家的路。一抹惆悵的晚霞,伴著你——一位憂郁的女孩兒,走過“白天鵝”極富魅力的門庭……
在紛亂的無奈籠罩著的小小閨房,你記掛著樂聲悠揚的“白天鵝”,涂抹著不敢讓媽媽發現的日記——好一個失意的周末。
隨意的裙裝點染著你——一個詩意的女孩兒。你夢樣的雙眸,流泄著夢樣的心境。
書是看不下去了。遠眺西天一抹紅云,你真想寫詩,寫一首如夢的詩。踱著散漫的步子,你陶醉在自己的夢中……
迎面走來的青年男子,向你投來一束強烈的目光。你從夢中醒來,象只警驚的羊羔。
他看著被你緊貼胸前的《朦朧詩集》發問:
“你也喜歡詩?喜歡舒婷?北島?還是顧城?”
你搖搖頭,疑狐地看著他,把書藏在身后。
“你很美,象首詩,你知道嗎?”
紅云遍布你柔嫩的臉龐。雖然你知道自己很美,可一個好女孩兒,怎能隨意接受陌生男子的夸贊呢?你本能地寫滿一臉的反感,隨口一聲“無聊”,轉身甩下一臉尷尬的青年,疾風樣逃去……
雖然,你也想和一位知音在傍晚的林子里談詩,談理想,談人生,可誰讓你是個女孩兒呢?女孩兒,就只能守著閨房,孤芳自賞——小鏡中一個滿臉寂寥的女孩子。
冬天,你想到北國去看雪,身著紅色的羽絨服,你踏上了北去的列車。
臨窗坐著無言的你,田野是一掠而過的蒼涼,給你的心劃下莫名的愁緒。假如有一位好友相伴;假如此時你能對別人說,或是別人對你說……你把目光轉向周圍的陌生人,你決沒有勇氣向任何一位開口。偏過頭,你只有把一腔的寂寞,寄托給一片寂寞的原野,在內心勾勒著一幅寂寞的畫。
對面一位男士看你很久。他讀著你的表情,讀著你的心。許是怕驚動沉思的你,你無語地推過一本書,是翻開的,上面有一句是用筆畫了紅線的:“壓迫著我的到底是我的想要外出的靈魂呢,還是那世界的靈魂,敲著我心的門,要想進來呢?”你一看便知是泰戈爾的詩。你猜想這已翻得很舊的書的主人,一定是非常的沉練。你悄悄抬起頭,想證實自己的猜測,正與他的目光相遇。那眼鏡后的深沉告訴你,他是一位有修養的知識男子。你的確很想捧讀這本書,它正和你此時的心緒相諧。可因為他是陌生人,你不得不縮回你小小的“殼”內。你知道,好女孩兒,不能隨意和不相識的人溝通;好女孩兒,應處處提防,以保護自己。你壓抑著自己“非分”的愿望,不盡情理地把書無聲地推過去。
他看著你:“不喜歡么?我想你應該喜歡的。”
你默默地看著他,不掩飾目光中流露出的提防。
“你以為,人人都心懷叵測么?”盡管,他的聲音很平和,卻有一種被曲解的不滿。
你無奈地低下頭,你知道自己不能對他解釋什么,也不可能對他解釋清什么。
北國,固然很美;很壯麗。你充分地欣賞了雪的潔白,更深地感到了北國之冬的靜寂。你曾夢想過在一片無垠的雪野上,踏兩行清晰的腳印,那一定是一首純情的詩。你的夢境實現了。當你就要離開北國南歸時,你回身望著一派空茫的雪野上,那兩行腳窩,你沒有絲毫欣悅之感。一種天地太大,你卻太小,太孤獨的悲涼襲上心頭。為了那份孤獨,你真想哭,真想大聲地哭。不再去管,如此瘋狂地發泄是否屬于“好女孩兒”。
你是好女孩兒,為了那一句句空空的嘉獎,你使他們如愿地把你囚在界墻之內,讓一腔澎湃的心潮,拍濺著緊閉的心門,把憂郁和清涼,寫在你稚嫩卻沒有歡樂的臉龐,枯萎了思想奔放的春花。
生活是多彩的,生命是短暫的。女孩兒,你何須界墻高高呢?
(于傳強王建華摘自《八小時以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