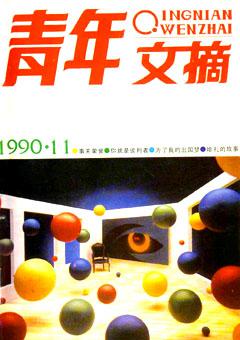爸爸會做的
〔美〕蘇珊娜·蔡辛 李青峰
爸爸小時候從沒有過一個真正的家。他五歲喪母,祖父再沒續弦。八歲時爸爸已在三個國家生活過。
可能這便是他喜歡制作和修理的原因。
爸爸常常修修補補。他六歲時——當時在土耳其——就曾將餐桌桌腿給鋸掉半截,那樣他便可以吃飯時坐得舒服些。為此他被懲罰,但他認識到了靠自己的雙手去處理問題的價值。
十歲時,在紐約布魯克林區爸爸曾用廢棄件組裝了一輛自行車。二十多歲時,他又裝了一輛用壞的汽車。他日夜忙碌,用他那大手輕輕地在各部件上涂潤滑油、調試。最終那輛轎車平緩地駛在路上,與那些富家子弟的車沒有兩樣。
爸爸是個實干家。他不懂微積分,但能說出鍋爐的工作壓強。他不會畫施工圖,但能告訴你管道和電線是否滿足要求。他上夜校后成為工程師,但在這之前他已干過管道工、電工和機修工。
爸爸為他多年制作的東西自豪。對我來說,什么都比不上他親手專為我做的那件小玩意兒。
那年快圣誕節時,我和爸爸經過一個玩具店櫥窗。櫥窗角有一個我所看見過的最棒的玩偶木屋。它的形狀象個停止滾動的圓木。小巧玲瓏的橢圓窗戶直鑿進去,里面還掛著花布窗簾,窗戶外還有一個小陽臺。
“嗬!爸爸,”我說,“你看這小木屋漂亮嗎?你說圣誕老人會不會送給我一個這樣的小木屋?”
爸爸看了一眼價格標牌:100美元。這在當時是筆不小的數目。“我看就是圣誕老人也買不起,”他打趣道,隨手往上提了提腰帶——他感到不安時總這樣,“或許會的,小寶貝兒。”
圣誕節,我一大早就醒了跑下樓去。晨光微弱,我在樹下看到許多各色各樣的包起來的小盒子——但都沒我鐘愛的那個小木屋大。爸爸覺察到了我的失望。他把我抱在膝上,輕聲告訴我,他小時候特想要一個紅色玩具車,可家里買不起。
“那你怎么辦呢?”我問。
“我用木頭和揀來的小輪子自己做。”他說,“你猜怎么著?我自做的玩具車比買來的玩起來還帶勁。”
“可我不知道怎么做小木屋啊。”我說。
“好,我們一起做一個。”他答應我。于是就在圣誕節第二天,爸爸放下家里未完的活兒,我們就干開了一夜接一夜,爸爸下班后精疲力盡,但總要抽出空做一會兒小木屋。
前前后后爸爸總共辛苦了四個月。但那個小木屋是一個孩子可以奢求的最珍貴的禮物。
多年以后,我離家到伊利諾斯州上大學。
那年3月份,爸爸媽媽專程來看我。我領他們到學校所在的城市散步,指給他們我最喜歡光顧的餐館和商店。
我們駐足在一個商店櫥窗前,櫥窗內擺滿各種手工油漆的木制工藝品。“這是一家奧地利商店”,我告訴爸媽,“里面有您曾見過的最漂亮的家具。”
爸媽很感興趣,隨我走入里面。在商店最里面有一個很高的裝璜華麗的橡木櫥柜。爸爸仔細察看著這櫥柜。“我能給你做一個同樣的柜子。”他說。
“哎呀,爸爸!”我說,“這不是一般的柜子。這是精制品。況且,你也做不了這么好。這是件藝術品。”爸爸的雙手從他正察看的抽屜上抽了回來。默默地,他關上柜子,走了出去——他的樣子仿佛一個男孩從剛拒絕他約會的美麗女孩身邊走開。我意識到傷害了爸爸的感情,但我怎么也難以承認爸爸能做出這樣的柜子。待爸媽回家時,這場不愉快似乎已被忘掉了。
三個月后,我結束了大學一年級的學習回到家里。家里的一切好象沒變。
我奔向樓上我的房間。迎面發現了一個大櫥柜,靜立在午后金色的陽光中,與奧地利商店的那個幾乎毫無二致。
我之所以說“幾乎”,是因為這個柜子在一些地方還略高一籌。前面的柜門由零木板拼成,不是橡木,但柜子精心的多層油漆竟使其產生古器般的色澤和氣氛。門上同樣漆著鮮花,花的上下兩端還有小白鴿。
我轉過身去,爸爸正猶豫不決地看著我,向上提了提腰帶。
“嗬,爸爸!”我說,從小到大沒這么親昵地稱呼他,“這柜子太美了。”
他走上前來用胳膊攬著我。他的指頭上還帶有沒有痊愈的傷口和擦痕,那是他多少日子辛苦制作這個柜子的見證。
“你的老父親畢竟是長于一些事的。”他微笑著說。話畢他急切地打開柜門給我看他改進的地方——這是爸爸的特點。柜子里,爸爸做了個暗抽屜。“你放珠寶用。”他向我解釋。他還在底部大抽屜里裝了一塊木板可以將大抽屜拆開。“這樣你要搬走時,就可以容易些。”爸爸說。
“爸,我永遠不離開您。”我條件反射般突口而出。
“可我希望你走,”他說,“我可以制做許多東西,但我無法構筑你的生活。我所能做的只是幫助你過你自己的生活。”
爸爸不給我寫信。他常常忘記我的生日或結婚紀念日——有時竟然忘了我的年齡。
但是,我只需環顧四周,便能感到他對我的愛。
我最最熟悉的一句話是以下五個字:“爸爸會做的”。他一生中都在為我制作、修理、改進對我最有價值的東西。爸爸給了我一個父親能給孩子的最寶貴的財富——他生命的一部分。
(李青峰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