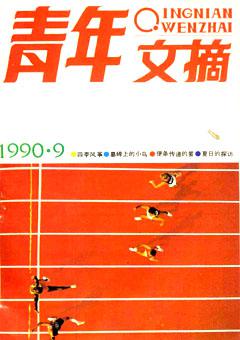再見,孩子!
〔美〕約翰·赫貝爾 鄭 然
“哎,他自語道,“該走啦。”聲音低沉。
這是十月里一個清新明媚的早晨。春天畢業后,他找了一夏天的工作,終于在兩千英里外找到了一份。直到昨天他告訴我們,他的女友凱西已同意和他結婚,我和他母親才真正明白,那種我們一起生活的時光已經結束。
我感到吃驚,他是我們的孩子,他一直在這兒,他屬于這兒,怎么他一下子長大了,要飛走了?
這就是那個在產院中第一次見到的孩子?他已長得這么高、這么漂亮自信。東西早已收拾好,放到了車上。他就要離去。他正走過小院,就在這兒,他不知玩爛了多少個棒球、足球;在這兒,他們那幫小家伙們還玩過牛仔和印第安人的游戲。這些如今都已成了他的記憶。遙遠的地方,機會正在等待他。
我清楚地記得他第一次上學的那天。早上,他穿著整齊的校服,看上實際年齡要顯得大。他要到一個完全陌生的環境中接觸全新的生活。走進校門,他不肯站進一年級的行列中,他哭了,他一點也不顯大了,他的確就是個孩子。后來在我們的鼓勵下,他擦干眼淚、走到了隊伍中。幾天后,他開始有了新朋友。這是他第一次知道他得有應付變化的能力。
開頭,他是個好學生,可他后來迷上了體育。再后來,他只把學校看成是舉辦各種體育活動的一個場所。
一個周五的晚上,校長掛來電話,說我的兒子對八年級“科學”這門課一點也不用功,而考試下周二就要進行。如果不好好復習,他很可能會不及格。
我們發生了一場爭論。他說他晚上不能做功課,他有場重要的曲棍球賽。我說他不能參加那場比賽,他眼下最重要的是做功課。他堅持他非去不可,那個隊全指望著他。我說那個隊要指望他可就錯了,因為他顯然不稱職。忽視了學校功課的人,是沒資格進球隊的;而如果他考不及格,整個賽季的比賽就更沒資格參加。
“我恨科學!”他咆哮著,瞪著我,恨我更甚于科學。幾天內我們不再是朋友了。但整個周末他都在弄功課。他終于通過了。
高中對他來講很輕松。“他從來不回家看書。”我向他的輔導老師抱怨道。“我從未看過他的學習。”“不要為這個孩子擔心。我們不想給他們太多負擔。你放心,他是真正的大學苗子。”輔導老師雖這樣說,但我仍然著急。我經常埋怨他功課沒考好,催著他把電視關掉好好學習。他成績很好,但我從不滿足。我擔心他不能獲得上大學后所需的學習方法。
他終于給我帶回了榮譽。然而,他進了大學,又迷上了社會工作。有時,他回到家中天都要亮了,我就在門口堵著他。那場面非常緊張。我一說話他就大步走開,并咕噥說希望我不要象對待孩子那樣對待他,我給他答復道,只有他自己別再象個孩子,我才能象他所期望的那樣去做。
第一學年末,他被處以去讀預科。我告訴他,如果他還想念下去,他得自己去掙學費。為此,他恨了我好一陣。我希望他用自己掙來的錢交學費,會使他更加珍視其中的價值。
這也許是我對他做的最有用的一件事。他在假期里干了許多重活兒,象建筑工及飲料廠的夜班等。他攢夠了學費還買了一輛車。
他的成績提高了,他還獲得了一種成就感。一次他說:“你是對的,爸爸。中學時我沒有學到怎樣去學習。”但現在,他教會了他自己。
他學會了安排時間。他能抽空打棒球,還當上了一名兼職推銷員。有時,他還找我討論一些他感興趣的歷史問題。那時光有多美好!
但是他要走了。他從院里走了回來。與我們握手擁抱。對我來講最好什么也不說。他母親抽泣著與他擁抱告別。
他的車開走了。在街道的拐角處,他停下來,笑著又揮揮手。我們也向他揮手。心中念著:再見,我的孩子!
(何曉兵摘自《西藏青年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