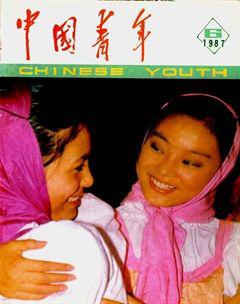知識產權、冒牌貨與法
大約是語言學家王力先生所說,寫文章分兩種:一種是寫而不賣,一種是賣而不寫。李杜蘇辛的詩詞可能屬前者。是否“藏之名山”,未知,但絕無沿街叫賣之事。若李白擺攤,以一字千金計,《蜀道難》定可致大富。作家而成職業,作文而兌現鈔,是晚近的事,和古之“潤筆”并不相同。按字計酬,按篇索費,是文藝作品和學術作品作為一種特殊商品出現才開始的。這就使賣而不寫的現象被大家注意起來。既不寫,何能賣?情況的確復雜。一種是徹底的賣而不寫。所賣何物:試將王蒙換汪夢,汪夢乃爾大名;且把屠格涅夫換司馬文峰,汝卻不著一字。下筆萬言,貝婁之抒情,契訶夫之狀物,川端康成之心理分析,悉收筆下,大段照抄,整塊拼裝……多快好省拿稿費。但此般技術,頗為危險,殊為少見。一種是,半徹底地抄,此法精義,在于巧奪:抄情節、抄人物、抄觀點……擬將北海道雪紛紛,化作漠河鎮紛紛雪;且看論者侃侃,原來都是普列高津論文提綱,用此種方式追名逐利,真偽難辨,法有不逮之處,故而諸多效尤,一時泛濫。
另一方面,由于復制錄制日見發達,不僅作者有被竊之虞,出版商亦頻涉被盜之危。中央電視臺春節聯歡會尚未播映,早有精明的出版商在街頭兜售該晚會的歌、曲磁帶。一部暢銷小說付梓之際,已被人象偷高考試題一樣拋了出來,影印復印,以高于該,小說定價5倍以上的價格傾銷。對一般的消費者,這也許是無關宏旨的事;雖有被敲之感,但畢竟偶爾為之。但作為出版者,則是一筆多么大的經濟損失!你想,你辛辛苦苦組織的一臺節目,請作曲家,請歌手,請樂隊,做難以言表的復雜組織工作,這樣的勞動,原是可以有優厚補償的。現在好了,袖手者只須在你蘋果園的蘋果熟了的時候來采摘就是了。這樣的洗劫,你經得起么?這冤哉枉哉的事情,難道不應與盜財竊寶視為一般無二么?
詩文也好,書籍出版也好,我認為,至少在現在是具有商品屬性的。不然的話,為什么被采用的稿件要付薄酬,為什么書肆里的圖書都有定價。讀者要汲取精神食糧,就如同要用人民幣買米買面一樣。這和我們所厭惡的“商品化”的說法是不同的。“商品化”是指,寫作、出版甚至包括演出,全不顧世道人心,一味地撈錢。譬如,那種思想膚淺、格調低下、用戀用愛用尸案用艷史掏讀者腰包的就是。即使如此,凡屬于被買的稿子,被賣的書籍,都具有商品的屬性。既然是商品,就有經濟利益關系;既有利益關系,也就同樣有了法的關系。我們以往處理這種事,聲討多于制裁,是一大欠缺。某人直接地或間接地抄了別人的作品,眾人異口同聲地罵他“文抄公”就是了。賠償乃至加倍賠償的事極為罕見。而象復印、翻制之類的事,簡直就不算是樁事。我發現,舊的圖書多半注有“版權所有,翻印必究”;而新的圖書,卻幾乎沒這條規定。興許是覺得此番標注,未免小氣,大有壟斷文化成果之嫌疑。細一想,不盡然。這很可能與我們在這方面仍缺法這根弦有關。我不知道現在有沒有一部出版法,但 一定應該有是鐵定無疑的。不然,這類訟爭會沒完沒了,也無所遵循,文化大盜小盜也就愈發猖狂。
涉及智能、知識、技能方面的成果,大都有這種問題。據我所知,國外的一些技術竅門,我們得花錢買。因為涉外,是純粹的買賣關系,所以也無話可說。即使國內,恐怕也有個技術專利權問題。或許有人說,專利云云,豈不是“技術封鎖”。問題并不這么簡單。上學,是要交學費的,你怎么能說這是文化封鎖呢?同理,一個企業或研究所花了時間花了錢,好不容易發明一項技術,你抄走圖紙資料就去生產,就去賺錢,合適么?你要學,對不起,請花錢買。否則,誰還愿意花錢搞科研,賠本搞發明呢?又譬如,一鄉辦啤酒廠,酒賣不出去,于是開印“五星啤酒”的商標,貼上賣,合適么?且不說達不到“五星”質量,即使是達到乃至超過“五星啤酒”,也不能如此張冠李戴啊。這種例子,不勝枚舉。
版權、專利、商標等等諸法,是為了制裁侵權行為,保護當事人利益的。這些法的實施肯定會有助于社會商品經濟的健康發展。否則,就杜絕不了冒牌名著,冒牌五糧液,冒牌發明家……
米博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