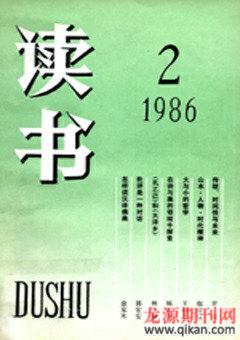立足于時代思潮的前沿
宋耀良
近代以來的文化或文學史表明,大凡努力把握時代脈搏的刊物,對社會時代思潮的發展,都會產生相當的影響與作用。不能設想,當初假如沒有刊物愿意發表愛因斯坦的第一篇論文——據說那時全歐洲只有幾個人能讀懂,恐怕二十世紀初的那一場物理學革命會被推遲。有時代責任感的刊物,是時代新思潮的后盾,尤其是新思潮的前沿陣地。從文藝理論刊物《當代文藝思潮》的編輯宗旨和發展趨勢看,它是在往這個方向努力的。
《當代文藝思潮》一九八二年才編出第一期,但短短的幾年內便在文藝或文藝理論界,尤其是文科大學生中產生了頗為不小的影響。當然這首先在于文學的解放和時代的開放。這家刊物可以說是生逢其時。新時期日漸生長起來的新審美欲求與藝術哲學思想,使讀者產生了了解文藝新思潮的愿望。而在這樣的思潮中又混合著歷史與當代、東方與西方、現實與現代等各種觀念的抵觸與沖突。新意識的萌芽,包裹在舊理論的框架中,舊思想又殘存在新的美學體系中。這使得我們當代文藝新思潮顯著地呈現出變革和過渡時期的特征——爭鳴、探索、創造和需要反省。
刊物在努力把握住正確流向的基礎上,幫助讀者了解新思潮,掌握新思潮。尤其是組織了一系列文藝現狀的考察和群眾審美狀況的最基礎的調查。這不僅是在有意識地為研究積累原始資料和數據,而且這種思考的方法,自身也體現出了當代意識。以往我們的文學史,往往只是作品史。其實,一個國家或一定時期的文學發展,最終是受到社會審美基礎的狀況所制約的。時代文學的動機,深藏在這具有整體性特征的民眾的深層原型之中。作品只不過是這種原型意識放出來的風箏而已。從這個意義上說,榮格稱詩人是“集體的人,人類潛意識活動的靈魂的傳達者和形成者”。文學史,如果不記錄整個民族審美基礎方面的變遷和演衍,實在是淺顯和空靈了一些。但以往沒有這方面的資料積累,史家只得拿農民起義或政治、經濟方面的資料來抵充。《當代文藝思潮》發表的一組附有統計記錄的調查報告,如《大學生與電影》、《關于當代青年工人文化審美傾向的考察——天津、蘭州等市的調查》等等,在當代文學的研究資料方面填補了一部分空白。可以相信,這種調查的數據,會因其最能直接體現這一時期審美意識的演變,而被后人珍視。
敢于支持作者標新立說,也是《當代文藝思潮》的一大特征。在急驟變革的時代,對理論自身價值的認識觀念也在變更。盡善盡美不僅不可能,也意味著生命和活力的終止。以往理論界對新學說的那種苛求,在很大程度上是“大一統”思想在方法論觀念中殘存的體現。每一個學說必須能說明一切問題,解釋一切現象,否則就不是新學說。對新學說的苛求與對舊體系的寬容是這觀念的兩個方面。由此這種龐雜完善的新體系始終沒出現,陳舊的體系卻一再延續。《當代文藝思潮》扶植了相當一批新學說的提出,陡然推起了一個勢頭,如“藝術創造工程”理論、“詩歌信息系統概論”、“文藝理論悖論論”。這些理論肯定是不完善的,在很多方面也值得研究和探討。但這些新理論提出的本身就已經產生了效應。它推動了理論界的創新之風,激發了創造激情和欲望。以“過程論”為范式的關于運動的觀點,體現在刊物的編輯思想之中。當然,現在只能是處于無數局部突破和積累過程中,但量變必定會帶來質變。《當代文藝思潮》清醒地為著理性思維成熟的時代到來,而鑄造著新思潮的思維材料,并以這為使命,這也為其在理論刊物的領域中奠定著厚實的基礎,構塑著自身獨特的形象。
《當代文藝思潮》與另外兩家大型文藝理論刊物《文學評論》和《文藝理論研究》形成了中國文藝理論界的三個點,三者各具特色。《文學評論》無疑是有著較高程度的權威性;《文藝理論研究》帶有學院式的厚重穩固的特點,更注重經典性;相比較,《當代文藝思潮》則處在當代文藝思想的最前沿,體現出理論的敏銳性和反饋的迅捷性。
迅捷性自然也有其短處,但我們偌大一個國家應當有一個以新理論探索為特征的陣地,尤其應當有一個供“新人”立言的場所,這無疑是必需的。《當代文藝思潮》正是在這個意義上注重扶植新人,所刊用文章的作者大部分是新人,不少是文科的在校學生。據初步統計,它從一九八二年創刊到八四年底的三年間,共刊發了三百八十人(次)的文章,其中作者兩次復出率僅占總數的百分之零點五,有十九人;三次復出率更小,只有六人;四次復出一人。這須有很可貴的精神和很自覺的認識方能如此。
銓察其創刊來的歷史,自然也有失誤和令人遺憾之處。從“疾風知勁草”的古訓中延伸過來,我以為,也許衡量任何一家刊物的一個重要標準應該是:不在于其在順境中對新理論、新觀點的熱衷程度,而在于逆境時對這些理論中合理成份的堅持程度。一家理論探索刊物不僅僅應當是當代新思潮的前沿陣地,還應當是堅固的堡壘。在這塊陣地上,不僅應聚集起新生力量,而且還應當保護他們進行正常理論論辯的權利。遺憾的是《當代文藝思潮》在處理這個問題上是有失誤之處的。在對某些的確有可探討和可批評之處的文章或觀點進行討論或批評時,沒有嚴格區分藝術理論探討與政治問題之間的界限,而且還延續了過去那種在政治上逐期“升級”的作法,這實在有點令人哀傷。由此使人想起十九世紀五十年代俄羅斯進步刊物《現代人》所面臨的一場挑戰。大作家屠格涅夫認為在杜勃羅留波夫評論他的小說《前夜》的論文中有號召反對沙皇之嫌,因而反對該文發表,并給主編送去了一封信,只有兩句話:“任你選擇:我或者杜勃羅留波夫。”一方是剛從學校畢業的二十三歲青年批評家,另一方是文壇盟主,周圍聚集著當時俄國最有影響的作家們,《現代人》也是靠他們支撐起來的。但主編涅克拉索夫想到的卻是刊物的編輯思想和宗旨。毅然決定發表評論。屠格涅夫、托爾斯泰、岡察洛夫等立即脫離了《現代人》。《現代人》非但沒垮掉,反而贏得空前贊譽,訂戶激增。
也許,從國情、時代、性質等許多方面來說,都不能進行簡單類比。但有一點是相通的,既然希望自己成為時代思潮的前沿陣地,就一定也得是前沿陣地的堅固堡壘,對新思潮得堅持,對新人則應保護。當然,行為的堅定和自覺應來自理論的自信與理解的透徹。
愿《當代文藝思潮》能在時代思潮的發展中,更深刻地認清自己的使命,成為理論探索更有力的推動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