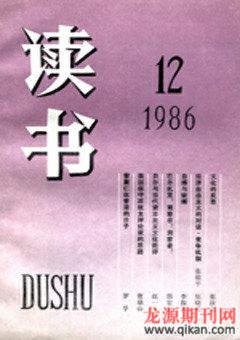文字的魔術師——克洛德·西蒙
王泰來 丁 聰
瑞典皇家學院將一九八五年度的諾貝爾文學獎授予法國新小說派作家克洛德·西蒙的決定宣布后,法國文化界曾掀起一場波瀾,許多報刊及文學評論雜志紛紛撰稿報道,大部分文章對法國文學受瑞典皇家學院冷落了二十多年以后,終于又有第十二位法國作家列入諾貝爾文學獎得獎人名單而感到欣喜,但也有少數文章卻冷嘲熱諷,甚至懷疑評選委員會中混進了奸細。當然大多數意見還是肯定這樣的選擇是從文學角度考慮的。
這次小小的風波也許會給我們帶來某種啟示。文學作品本來很難用劃一的標準來衡量,因為它千姿百態、變化多端,很難說一部作品絕對好,好到無可指摘;而另一部作品絕對壞,壞到一無是處。更何況諾貝爾文學獎從來也不是,也不可能是公認的評價文學作品的唯一標準,不過它無論如何是一種標志,一種傾向,一種對文學作品的評價,如果從這一角度看問題,那么這次獎金的頒發是值得深思的。
眾所周知,克洛德·西蒙屬法國新小說派的成員。經過五、六十年代在小說理論上、創作上的劇烈較量之后,一些不同于巴爾扎克式傳統創作方法的新小說作家站到了一起,他們人數不多,但活力很強,通過多次國際討論會,他們都一個個在公眾面前亮了相,并直言不諱地承認自己屬于新小說派,克洛德·西蒙就是其中之一。
盡管這批作家創作甚豐,理論卓著,但新小說在廣大公眾眼中卻始終沒有被當作正宗的文學來接受。隨著時間的推移,有一批新小說進入大學的課堂,讀者逐漸多起來;但從總體上說,新小說更多地是作為一門學科(文學科學)的研究對象。于是出現了這樣的現象,在一部分有較高文化水準的知識分子中,開始對新小說感興趣,并以它們為實例對小說理論、小說技巧進行了多方面的探討,但新小說始終被大多數公眾拒之門外,主要的原因是新小說的故事沒頭沒尾,既無曲折離奇的情節,亦無性格鮮明的人物,小說中時空跳躍不定,現實與想象不分,總之,新小說難讀、難懂。這種小說不再象有些傳統的小說,可以是藝術欣賞,又可以成為茶余飯后的消遣。新小說家在作品中所體現的某種追求,他們對小說內部結構的探索,他們對文字表達能力的大膽嘗試,這些都需要讀者集中精力,全力配合去體驗。這樣的閱讀就需要有一種探索的愿望,一種鉆研的精神。對一般讀者作這樣的要求,自然與他們對小說的理解并不吻合,因此,新小說自其誕生之日起,一直在各種非議、責難中掙扎,奮斗。八十年代以來,一些知名的新小說家紛紛寫帶有自傳性質的作品,如納塔麗·薩洛特的《童年》,瑪格麗特·杜拉的《情人》,阿蘭·羅伯—格里耶的《重現的明鏡》,于是不少評論家認為新小說的時代已經過去,似乎新小說已走到死胡同的盡頭,他們的根據是新小說家本身也回到寫自傳這樣傳統的創作道路上來了。于是一時間,新小說如同一切標新立異,追求新奇的事物一樣,象過眼煙云似的不留痕跡地逝去了這種說法廣為流傳。這種看法不僅國外有,國內也有。其實僅從題材和作品內容來判斷一種創作道路恐怕十分片面,只要認真讀讀作品就會得出比較公允的結論。因此這一觀點并沒有被人們普遍接受,但它卻堵住了大多數并不了解真實情況的人們的嘴。恰恰在這種時候,一種在世界范圍內享有權威的文學獎金偏偏頒發給一位處于“沒落”階段的新小說派的作家,這豈不催人深思。談到一九八五年度的文學獎,瑞典皇家學院對克洛德·西蒙作了這樣的評價:“兼有詩人與畫家的創造才情,在小說中致力于表現對時間的深刻意識和人類的處境。”這個評價是中肯的,從這短短數語中,可以看出瑞典皇家學院不僅肯定了克洛德·西蒙個人的創作,也肯定了新小說的某些特點,也許正是皇家學院對這種一直被認為是新奇的、非正宗文學的肯定才引出這場風波。
這場風波的另一重要原因恐怕要涉及克洛德·西蒙本身。西蒙在新小說家中并不引人注目,從創作歷史來說,他不如納塔麗·薩洛特資歷深,西蒙的第一部小說《作假的人》發表于戰后一九四五年,而薩洛特卻早在戰前就開始創作;從對新小說運動的貢獻來說,他不如阿蘭·羅伯—格里耶,里加杜,布托爾等人,也不如薩洛特,他們都有不少理論著作,從對小說的概念直至小說技巧都有詳盡的論述,他們的這些理論曾披荊斬棘為新小說的誕生與發展開辟道路,而西蒙除了創作外沒有發表過系統的理論;從所從事的文化活動范圍來看,他也不如羅伯—格里耶與杜拉,他們不僅寫小說,還寫電影腳本,甚至親自編導電影;從對公眾的影響來看,在世界范圍內公認的新小說派的領袖人物是阿蘭·羅伯—格里耶,這在不少國家所舉行的當今世界最著名和影響最大的作家的民意測驗中可以得到證實。在一九八五年年底以前,克洛德·西蒙可以說是一位勤于創作而又默默無聞的作家。諾貝爾文學獎頒發給一位幾乎是過著隱居生活的新小說家,在公眾中引起爭議原也在情理之中。
話要說回來,諾貝爾獎金的頒發也不是盲目的,讀過克洛德·西蒙作品的人會覺得他的創作自有一番刻苦、艱難的用意,其與眾不同的特色是顯而易見的。
新小說無重大意義的題材這種說法是不大確切的,確切地說應該是新小說家都力圖通過文字的組合或小說結構體現他們對當今世界或者某些問題的觀念,而很少直接反映具有重大意義的歷史的或現實的題材。但克洛德·西蒙卻有些例外。西蒙出生于馬達加斯加的首府塔那那利佛,他與法國存在主義著名作家加繆同庚,比一般的新小說家年長一輩。他經歷過影響本世紀命運的重大事件,在三十年代歐洲政治局勢動蕩不安的時刻,青年時期的西蒙并沒有作袖手旁觀的局外人,他積極參與了西班牙內戰,為西班牙共和國而奮斗。第二次世界大戰期間,他在騎兵團服役,親眼見到法軍不堪一擊的慘痛局面,親身經歷了大潰敗,并當了德國人的俘虜。影響歐洲人思想情緒的重大事件,他都身臨其境地體驗過。他豐富的閱歷,他在威脅人類命運的戰爭中所遭受的痛苦和磨練,使他的作品自有一番與別的新小說不同的境界與情趣。他似乎有一股不可遏止的欲望,要把他的痛苦經驗反映到作品中去。他的代表作之一《佛蘭德公路》(一九六○)就是以一九四○年五月法軍在法國北部接近比利時的佛蘭德地區被德軍擊潰而撤退為背景,描寫三個騎兵及其隊長痛苦的遭遇,全書以對全軍崩潰,對家庭生活的不幸——妻子的不忠懷著絕望心情的隊長雷謝克的死亡為主線寫出了在潰敗中普通士兵與老百姓所受到的痛苦,戰爭對大自然的摧殘等。西蒙的作品中涉及第二次世界大戰或四○年大潰退的還有《作假的人》(一九四五)《草》(一九五八)《豪華旅館》(一九六二)《教訓》(一九七五)和《農事詩》(一九八一)。他的另一部代表作,獲得一九六七年美迪西獎的《歷史》是一部熔作家的個人經驗與人類的群體經驗于一爐的作品。故事發生在二十四小時之內,通過一些極為平常普通的事件:一個人去銀行,遇見一個無賴,在餐館用午餐,把
西蒙年輕時曾在英國師從立體派畫家安德烈·洛特習畫,他的創作與繪畫有著密切的聯系。數十年來他刻意追求如何將文字藝術與繪畫藝術熔為一爐,如何使呈線形發展的文字達到繪畫的視覺效果。西蒙所指的視覺效果當然不是浪漫主義對迷人的景色的描寫,也不是巴拿斯派詩人所倡導的,通過精選詞句,使景物躍然紙上的那種造型美的效果,而是指從繪畫中得到啟示,力圖用繪畫的原則來進行創作,他說:“寫作如同畫家作畫一樣,就象畫家在作畫過程中這里添上一筆、那里抹上一層色彩會產生新的效果一樣。”驅使西蒙創作的愿望是不斷探索產生新效果的“這一筆”與“那一層色彩”,他說“只有通過想象,通過對技巧的想象,作家才能找到解決小說所遇到的困難的答案。”(《克洛德·西蒙問答》)他常常將繪畫的發展與小說的發展相比較,并力圖將現代繪畫的原則運用到小說創作中,當人們談到新小說難讀難懂時,他反駁說:“當人們第一次看到印象派繪畫——其中長著玫瑰色的樹干和藍色的樹葉——時,有人叫嚷說,從未有過這樣的樹。而我們現在看這些畫時,卻不覺得有什么異常之處。而且,在某種光線照射下,我們確實看到了長著玫瑰色樹干和藍色樹葉的樹。”(見一九七○年克洛德·西蒙答記者比羅·蒂埃巴赫)他在接受諾貝爾獎的答謝演說中又一次談到了這個問題:“當年那些在印象派畫中只看到粗糙亂涂的(即不堪卒讀的)輪廓的人的孫兒輩現在排著長隊去‘欣賞展覽會或博物館中同樣粗糙亂涂的作品。”這里提出了兩個問題,一是觀察事物的角度,一是習慣。人們習慣于某種觀察事物的角度,稍有改變,那事物就變成不可理喻。印象派的繪畫倒是很好的說明,莫奈的那八幅氣勢宏偉的《荷塘》以及他的四幅《盧昂大教堂》不是因為季節、氣候、時間的不同引起光源的變化而畫面迥然不同嗎?同一個荷塘以八幅不同的景色出現在畫面上,同一座教堂的正面以四種不同的色彩與光影出現在畫面上,這現象是否值得人們深思,同一事物由于觀察的時間、地點、角度的不同,其面貌是不同的,那么寫小說的角度不同,小說的面目也會不同。新的寫作角度需要新的閱讀習慣與方法。正如印象派繪畫的實質在其色彩的運用與光影效果一樣,克洛德·西蒙追求的是小說的實質——小說內部文字之間的相互聯系,詞語之間的相互呼應及和諧一致。“我建議象觀察三塊活動畫板組成的畫那樣去閱讀作品,這三塊畫板有時表現完全不同的場景,有時是統一的整體(如《圣人生平》),這類作品的同一性在于繪畫的實質,例如左邊畫板上端的紅色與右邊下端的某一紅色或者還與某一綠色相呼應,這樣三塊畫板就組成一個整體。這種色彩的和諧和色彩之間的相互呼應,就是《三折畫》這部作品的含義,至少我是這樣想的。”(《克洛德·西蒙》色麗齊討論會專集)以三折畫的原則來看文學作品的完整與統一,其關鍵并不在于有完整的故事或統一的情節,而是在文字之間相互反射、折射。呼應等聯系。談到他的具體創作過程時,他的小說《雙目失明的奧利翁》(一九七○)是受法國畫家布賽的繪畫《雙目失明的奧利翁面向旭日東升》啟示而寫就的。“我一直十分喜愛這幅畫,它標題的全文是《雙目失明的奧利翁面向旭日東升》,我覺得這是一個形象——怎么說呢,我不喜歡象征這個字——總之它很好地表現了我的創作過程。正如我在《雙目失明的奧利翁》的短短的前言中所談到的,我自己并不清楚向何處去,只是對著一個我自己還辨別不清的目標摸索著前進。”(見斯圖亞特·西蓋斯《論克洛德·西蒙的小說》)總之西蒙的小說是在創作過程中產生,在創作過程中完成的,根據文字、詞語的能量,受其魔力的支配,他的小說向四面八方伸延,西蒙認為這正是小說的本質所在,他在創作過程中刻意追求的便是這種具有魔力的文字及其最大限度的表現能量。
克洛德·西蒙這種執意的追求構成他小說的最大特色。打開西蒙的小說,一眼望去,馬上便會發現許多語言文字上的特點,例如《歷史》就是這樣開始的:
它們(她們)之一幾乎碰到房子夏日當我夜間在敞開的窗戶前工作到深夜時我能看到它(她)或者至少它(她)下面被燈照亮的枝杈以及那類似羽毛在黑暗深處微微跳動的樹葉……
這段話沒有標點,首先出現的代詞它(她)不知究竟指什么,要讀到第二頁結尾讀者才能肯定這代詞它(她)是指樹枝。在樹枝這名詞出現前,代詞它(她)曾再次出現,但它所指的已改為在殘敗的住宅中哼哼唧唧的老婦人了。由于這個代詞性數歸類中所可能包含的容量,作家象變魔術一樣,將這個詞一會兒指樹枝,一會兒指老婦人,于是小說便循著這代詞的不同所指,沿著不同的軌跡發展。在這短短幾行中出現了比喻(類似羽毛的樹葉),究竟是羽毛還是樹葉很難分辨,因為緊接的下文便從羽毛一詞引發到雀躍在樹叢間的小鳥,于是羽毛一詞變成既可指樹葉,又可指小鳥,文字的表現范疇擴展了。文章既從樹枝的代詞它(她)開始,自然談及樹,于是從樹又引伸出家族譜系圖(larbre généalogique與larbre(樹),詞語的主干相同)。這個片斷說明西蒙作品的一些特色,或許也可以說明西蒙的追求。他認為文字之間的呼應,其含義的轉換所構成的一種表現力才是文學作品的本質所在。對詩歌中不用標點,自從本世紀初阿波里奈開創以來,現在大家已經習以為常,至于通篇小說,甚至象《歷史》那樣長達四百余頁的長,篇也基本上不用標點,恐怕還是少見的,基本上不用句號,經常用省略號作為段落的結尾,而且常常句子中套句子但從來不用引號,凡此種種是否可以理解為便于文字之間彼此呼應,便于轉義,有利于讀者的聯想呢?
此外西蒙作品中其他特點也需要提一下,例如他大量使用現在分詞。現在分詞在法語語法中常常表示與主句的動作同時發生的動作,三個四個,有時甚至五個六個現在分詞并列使用,使人產生一種動作縱橫發展的空間感,把文字線形發展的局限打破了,拓闊了文字的表現面。西蒙作品中的段落常常在句子中間,甚或在一個詞的中間結束,而句子的另一半或詞的后面幾個字母則到以后再出現。這樣就形成整部作品呈螺旋形前進,每個敘事都不是一次完成,都需要不斷反復補充,形成不斷循環上升,每次反復都有一定的空間跨度。西蒙的這種空間結構與比托爾在《展現》(一九七三)中所表現的空間結構不同,后者是通過字體大小,字母排列疏密,字句在版面中所占據的空間以及所留空白來實現的,而西蒙的這種螺旋形結構則是通過字詞或句子的內部聯系——呼應、重復、同音異義,修辭中的比喻、轉義等——實現的。作品中時序顛倒的,隔列成一個個的小片斷就是通過作品的內在邏輯,通過文字的魔術般的表現力才得以組成一個整體。
西蒙在談及他的創作與傳統的小說不同時這樣說:“除了這種現實主義意圖的‘連續性之外(這種意圖完全是荒謬的,因為誰都知道,不管是多么傳統和‘現實主義的小說,沒有一部小說它的時間沒有經過縮短,拉長,切斷,壓縮或者人們所說的‘突然縮短,即完全不連貫等處理)……除去呈現在我們面前的這種虛構的以及全部接受下來的事件外,作品中沒有其他東西了”……他又說:作品的“內部邏輯既來自文字的音樂性(韻律,疊韻,句子的節奏)也來自它的物質材料(詞匯,“辭格”,轉義)。因為我們的語言不是隨便形成的。”
西蒙所追求的正是這種文學作品的內部邏輯,語言文字的魔力。一九八五年度的諾貝爾文學獎也許正是對克洛德·西蒙長期以來這種耐心而執著的追求的一種褒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