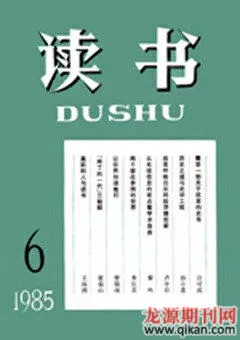值得歡迎的“劇作家專論”
匡亞明 丁 聰
董健同志的《陳白塵創作歷程論》,是一本用了很大功夫寫成的作家專論,頗有特色,值得向讀者推薦。而陳白塵同志又是我們敬佩的一位老朋友、老作家。對這樣一本著作的問世,我義不容辭應該說幾句話。
一九三四年,我和白塵同志在獄中相識。我倆被關在一間“斗室”之中,雖然失去了行動的自由,但鐵窗鎖不住我們的心。起初,互相不夠了解,不敢直接地深談現實的政治問題,但在歷史故事里我們找到了共鳴點。為了寄托交流、抒發那滿腔的悲憤之情,也為了排遣那與世隔絕的令人窒息的寂寞,我們在談論歷史人物的興奮中度過了漫長的日日夜夜,而其中說得最多的,就是石達開。我那時對這位雖然出身于士大夫階級,但終于走上農民革命道路的文武雙全的人物,懷著很大好感。我總是帶著惋惜的心情,來講述他的道德文章和戰斗生活,這就免不了在自己所記憶的史料的基礎上,加進一些合理的想象,使故事更為生動一點。對于石達開的一些詩(如《答曾國藩五首》),即使不一定是他親自寫的,由于多少也足以表達其人其情,所以也常常激昂慷慨地加以朗誦。白塵同志似乎也有同感。他說,將來一定要寫一部關于石達開的歷史劇。果然,他后來出獄不久,就寫了《石達開的末路》,后來又寫了反映太平天國前期革命斗爭的歷史劇《金田村》,并將《石達開的末路》改寫為《翼王石達開》(又名《大渡河》)。當我在解放區看到了這些著作時,回想起我們在獄中的一段交往,心中竊喜:“此公言而有信,朋友之誼深厚!”盡管他寫這些戲并不是為了我,但我卻不禁把這些戲看成我們患難之交的紀念了。那時我們已經天各一方,我不時從報上得知他在革命戲劇運動中時有建樹,快慰之意常溢于心!十年動亂中,白塵同志深遭誣陷和迫害,而《石達開的末路》又是“罪狀”之一,想不到我們的患難之交竟又成了他的罹難之由了。但那個可詛咒的時代終于過去了,我們又一起迎來了光明。
建國以后,白塵同志在文藝界,我在教育界。但粉碎“四人幫”之后,白塵卻成了一個教授兼作家,腳踏教育、文藝兩條船的人物。這個使他頗難處的處境是我造成的,因為一九七八年我邀請他到南京大學任教,主持中國語言文學系的工作,并建立了戲劇研究室。不知他是否怨我,但我至今不悔,因為頗有些經院習氣的大學文學系,是需要吹進一點新鮮活潑的空氣的。外國的不說,單就中國而論,魯迅、茅盾、田漢、老舍、郁達夫、洪深……等等有成就的作家,不是都曾任教于高等學府嗎?白塵同志到南京大學以后,雖然工作上困難很多,但他還是在創作上,教育上做出成績的。不僅有好的作品問世,而且他培養的研究生已經引起了戲劇界的注意和好評。最近又聽說他接受了國家任務,主編《中國現代戲劇史》,我祝他創作、研究雙豐收!
陳白塵同志是在我黨所領導的左翼文藝運動中成長起來的一個有成就的作家。尤其在話劇創作方面,幾十年來他做出了可貴的貢獻。正如董健同志的書中所說,在“中國現代劇作家的群星之中,陳白塵以其特有的光亮和位置而引人注目。”這樣一個作家,是值得我們研究的。孟子說:“頌其詩,讀其書,不知其人可乎?是以論其世也。”董健同志研究陳白塵,有一個“知人論世”好條件,也就是“近水樓臺先得月”,他在陳白塵領導的研究室里工作,日相處而甚相得,頗富師友之情,研究者與被研究者可以互相交心。當然,光靠這一點是不夠的,還必須對大量作品及有關史料進行深入細致的研究和分析,才能得出較為科學的結論。董健同志在這方面是下了一番功夫的。他的這本書,對陳白塵將近六十年的創作歷程,進行了比較全面系統的論述,對有代表性的作品進行了較為深入細致的剖析,并夾述夾議,對一些有爭論的問題提出了自己看法。我個人覺得,書中對陳白塵其人其作的論述和評價是深刻的、允當的。當然,全面認識一個作家是件很不容易的事,書中的評論,在某些方面也難免會出現寸出寸入、高低失當之處,這還有待學術界和廣大讀者的討論。但有一點可以肯定,即作者的態度是嚴肅、認真的。譬如,作者一方面對陳白塵懷著一種晚輩對長輩的很深的敬意,一方面在對他的創作歷程進行分析時,卻采取著一種頗為“苛刻”的態度,有好說好,有壞說壞,決不含糊。論及優點,剖判主深,力圖分析得頭頭是道;談到缺點,挑剔主透,盡量評說得絲絲入理。現在雖然還不能說作者在研究上已經完全達到了“深”與“透”,但我覺得他是在努力這樣做的。
孤立地看一個作家,很難看得清楚,只有把他放在特定的歷史環境中進行考察,才能認識他的真面貌,也才能比較準確地說出他之“然”與“所以然”的道理。此書注意從聯系和比較中對作家進行歷史的考察,我想這一點也是應該肯定的。書中不論是對作家的成就還是對他的問題進行分析時,都盡量把眼界擴展到當時整個文藝運動和社會思潮,試圖從歷史的土壤里挖掘出它們形成的原因,并從聯系和比較中抓到作家的個性。作者對陳白塵在我國現代諷刺喜劇和歷史劇創作上的獨特貢獻,就是以這種歷史眼光進行觀察和論述的,因而有助于我們認識陳白塵在現代戲劇史上“特有的光亮和位置”。尤其值得注意的是,作者還試圖把對個別作家的研究與對整個歷史教訓的總結結合起來。陳白塵是一個善于幽默和諷刺的喜劇家,他的《結婚進行曲》、《升官圖》等作品曾發生很大的社會影響,用“笑”的藝術教育和娛樂過很多觀眾和讀者,在反對國民黨反動統治的斗爭中發揮過積極的戰斗作用。但是建國以后,他為什么拿不出更好的喜劇作品呢?這里有復雜的社會原因,也有深刻的歷史教訓。作者對陳白塵在建國后創作“歉收”的主觀和客觀的原因,尤其對根深蒂固的“左”傾教條主義思潮對文藝創作的不良影響,進行了歷史的分析。這分析還不能說很充分、已經做到準確無誤,但我相信它對開闊讀者認識歷史的思路是大有裨益的。
所謂歷史的眼光,不單是意味著把一個作家放在特定的社會歷史背景下來研究,而且還要求把一個作家自身的發展變化,也當作一個歷史的過程來考察。看來,本書作者對這一點也給予了充分的注意。他既對作家的整個創作歷程及其特點進行了綜合分析,又對作家的藝術素質和創作個性,試圖進行歷史的發微和探源。孤立地看作家的某一部代表作,是看不清楚的。本書不是就作品論作品,而是把它作為作家整個創作發展歷程中的一個有機的環節,進行上下聯系和比較,從中探明這部作品形成的種種因素,擺正它的歷史地位,例如,作者研究了陳白塵歷史劇創作的發展過程,找出了這一過程中三個發展階段上各不相同的特征和貢獻,并史論結合地闡述了陳白塵歷史劇創作主張的發展變化,最后,又把他的史劇美學觀概括為歷史真實、藝術真實和現實傾向性的三統一,并用這個美學尺度去衡量他在不同時期歷史劇創作上的成敗優劣。同樣,書中對陳白塵喜劇創作的發展,也力圖把握到它的歷史線索。《升官圖》代表著陳白塵喜劇藝術的高峰,但它不是突然從天而降的。書中從陳白塵二十年代的小說中就挖掘出他喜劇家的素質,并對以后十幾年間他的諷刺藝術的發展進行了論述,從而闡明了《升官圖》的藝術淵源。這樣的歷史分析法值得提倡。
我認為,對于中國現代戲劇史,文學史的研究,應該建立在對一個個作家的深入細致的專題研究的基礎上,由個別到一般,由“微觀”到“宏觀”,這樣做才不致失之籠統,空泛,得出的歷史規律才是可靠的。歷史規律不是從研究者的頭腦里產生出來的,它具體體現在每一個作家不同的生活和創作道路中。只有用辯證唯物主義和歷史唯物主義的觀點,對大批作家進行深入的專題研究,才能總結歷史經驗,發現歷史規律,以指導今天的文藝實踐。目前我國對現代劇作家專題的書還不多見。在這種情況下,我覺得董健同志的《陳白塵創作歷程論》的出現,是值得歡迎的。我希望有更多的劇作家專論出版。
一九八三年六月三十日于南京
(《陳白塵創作歷程論》將由中國戲劇出版社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