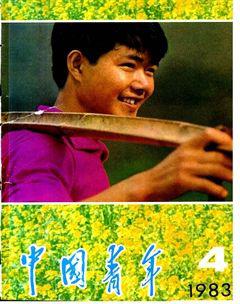小溪(小說)
張為 趙曙光
一個(gè)護(hù)士死了,醫(yī)院的人們也許會(huì)惋惜。她雖然剛從軍醫(yī)學(xué)校分來不到一年,有人說不定還拿她的名字對(duì)不上號(hào),但她畢竟太年輕。據(jù)說還不滿十九歲。
可是如果聽說她護(hù)理過的病號(hào)竟然夜里悄悄跑到太平間外面,頂著露水和涼氣為她守靈,工作人員勸也勸不回去,大家又會(huì)怎么看呢?
六五一結(jié)核病院的總值班日記上,確確實(shí)實(shí)記載著這樣的事。關(guān)于守靈,據(jù)說起初是夜班護(hù)士電話報(bào)告“四個(gè)病員失蹤”。總值班員不得不從床上爬起來,還為“結(jié)核病員難管理”大感頭痛。可是在找到了他們,勸他們回去休息的時(shí)候,他卻被那個(gè)場(chǎng)面弄得鼻子發(fā)酸了……
“感情”這個(gè)詞幾
楊大成一入院就對(duì)王小清發(fā)怒,這只是因?yàn)樗械奖餁狻T缟媳讳摻z床嘎嘎吱吱的響聲吵醒,他猛地想起是躺在醫(yī)院里,心里一沉,就怒了。
他原是艦隊(duì)里公認(rèn)的“標(biāo)準(zhǔn)水兵體魄”。可就是一張輕飄飄的診斷書,就把他弄進(jìn)了醫(yī)院。
弄得鋼絲床響的,是那個(gè)叫梁黑子的新兵。他好象還在連隊(duì),搶先起床穿衣服,很響地走進(jìn)走出,掃地,拖地板,給別人打洗臉?biāo)=又莻€(gè)叫朱銳的就連忙起床,一邊說:“哎呀哎呀,我又起晚了。”一邊和梁黑子搶活兒干。他也是個(gè)倒霉蛋,剛從高中考進(jìn)軍政學(xué)校,沒學(xué)到一年就搬到醫(yī)院來了。梁黑子用快活的河南調(diào)兒回答:“中,中,您都請(qǐng)歇著。”
“又裝什么假積極,不怕人討厭!”
這一位是要塞區(qū)的觀測(cè)兵劉玉,是個(gè)留小胡子,愛照鏡子,愛哼“甜蜜的愛情從哪里來”的角色。據(jù)他自己介紹,他是因?yàn)樘郊页思伲结t(yī)院想混個(gè)病假條搪塞搪塞,不料倒真查出了肺結(jié)核。如今他已經(jīng)是第二次住院,講起往事還滿臉得意,好象因禍得福了。
“也沒人晚點(diǎn)名表揚(yáng)你們,也撈不著立功受獎(jiǎng),一大早撲撲騰騰的,吵人家睡覺!”他喝斥完了兩個(gè)做好事的,又蒙上頭。
梁黑子不敢動(dòng)了。朱銳對(duì)著被子說:“身體有病,精神不能有病嘛。撈不到好處就不學(xué)雷鋒啦?”
“得啦得啦,”劉玉又伸出頭,“有病就要多休息。怎么的,是雷鋒叫你們來吵得別人不能休息的?”
這亂糟糟的地方!楊大成更煩了。連吸幾口煙。
走廊里響起了送藥小車車軸的吱吱聲。這回劉玉起床了。門開處,一個(gè)小護(hù)士推門進(jìn)來。楊大成斜眼看她,個(gè)子不到自己的肩頭,肥大的工作服在身上直晃蕩;尤其可笑的是那頂圓圓的護(hù)士帽,松松垮垮地扣在頭上,老象要掉下來。她就是王小清。
劉玉對(duì)她滿臉堆笑:“王護(hù)士,今天是搓棉花簽兒還是起瓶蓋兒?等你指示啊!”
王小清歪歪身子,斜斜大口罩上的兩只黑眼睛,嬌聲嬌氣地一笑:“你呀,剃頭刮胡子去!”
“我請(qǐng)問,留兩根胡子到底算什么錯(cuò)誤?”
“資產(chǎn)階級(jí)生活方式唄!”
“那好哇,我請(qǐng)問了:馬恩列斯都留胡子,你王小清小姐怎么打發(fā)他們四位?”
“他們要是參加解放軍哪,保險(xiǎn)都剃了。”劉玉噎住了,朱銳和梁黑子都樂了。楊大成一沉臉:有什么可笑的!他披上衣,推門上陽臺(tái)去了。
陽臺(tái)上染著初夏明媚的陽光。楊大成一低頭,看見樓下面居然有一條小溪。它滑過一道黃沙鋪底的淺溝,漫進(jìn)一片嫩綠的草灘,濃密的草縫里到處閃射出斑斑點(diǎn)點(diǎn)的光亮。從那里隱隱傳來淙淙的水聲。
“你也喜歡這條小溪?”
王小清不知什么時(shí)候跟出來了。楊大成不友好地掃她一眼。他看見了一雙亮亮的、睫毛向上揚(yáng)起來的、孩子般的黑眼睛。
“它真好看,是不是?你要是想家了呀,看看它,心里就好受了。”
這算什么話?堂堂的海軍老戰(zhàn)士是讓人當(dāng)孩子哄的嗎?楊大成怒氣升上來,直拱腦門子。
“呀,你好傻呀!”王小清大驚小怪地嚷起來,“都肺結(jié)核了,你還抽煙!”
楊大成不理她,又摸出一支,就著煙屁股續(xù)上,然后深深吸一口,長(zhǎng)長(zhǎng)地吐出來。
她卻笑了,黑眼睛透出稚氣:“你象我二哥,也是牛脾氣。”她遞上一只藥杯,“我媽老罵他‘犟脖子牛。吃藥吧,別抽煙了,真的。”
她的手又小又瘦,白極了,卻沒有光澤,手背上看得見粉紅色的毛細(xì)血管。楊大成把臉扭到一邊。
“給呀!”王小清抓過他的大手,把藥倒進(jìn)他手心里。
楊大成沒料到她竟會(huì)動(dòng)手動(dòng)腳。他真火了,把藥片狠狠地摔在地上,牛一樣瞪著王小清。王小清怔怔地望著他,淡淡的紅暈從口罩里爬出來,在眼睛底下散開,黑眼睛里也包上了亮亮的淚光。
陽臺(tái)上的響聲引出了三個(gè)病友。劉玉問了聲:“怎么回事”。王小清低下頭,輕聲說:“沒什么,是P、A、S的糖衣掉了,怕有點(diǎn)變質(zhì)。我再去換。”
她低著頭推著車出去了,過一會(huì)又低著頭拿來了藥,把藥和藥杯都放到了楊大成的床頭柜上。
然而這一次的交惡卻沒有斷絕兩人的接觸。楊大成不吃藥,不蓋被子,為所欲為地對(duì)身體采取破壞性措施,果然招來了肺結(jié)核真正的懲罰。他發(fā)燒了,劇烈地咳嗽,而且咳出了血。他被移進(jìn)了急救室,插上了氧氣,吊上了靜脈滴注針。如果換了別人,也許會(huì)為這境遇傷心。可他只會(huì)發(fā)怒,他不信這倒霉的肺結(jié)核能最后撂倒他。“怕個(gè)鬼,肺癌才好呢!”他真象一頭身上插滿了刀的西班牙斗牛,拼命沖向最后一把刀。在白天繁復(fù)的會(huì)診、檢查、治療之后,夜里,他趁值班護(hù)士離開之機(jī),拔掉了輸氧管,拔掉了輸液針。
“你這是干什么呀?”值班護(hù)士沒隔一會(huì)兒又來了。是王小清。
楊大成冷冷地一笑,扭臉不理她。
她撲過來,迅速把輸氧管插進(jìn)他的鼻孔,可他又把它拔下來了。她說:“你怎么能這樣呢?”放下正整理的輸液針又來插管,他干脆把她推開,低聲吼道:“討厭,滾開!”
他一翻身,背朝著她,猛咳了一陣,閉上了眼睛。他感到胸悶,胸痛,渾身酸脹。他太疲倦了,恍惚中,他好象見到了他五歲時(shí)就死去的母親。這是他幼時(shí)生過的一場(chǎng)大病留下的印象:他躺在母親懷里,奄奄一息,望著母親抱著他流淚、抽泣……
抽泣的聲音使他驚醒了。站在床邊的是王小清。她沒戴口罩,手里捏著輸氧管,眼淚順著小鼻子小嘴流到下巴尖兒上吊著。見楊大成翻過身來,她帶著哭腔說:“都怪我,你一住院我就惹你生氣了!可是你不要這樣,好不好?”
一股熱浪打上來,楊大成那顆石頭般的心動(dòng)了一下。他感到眼皮子發(fā)澀,連忙慌亂地點(diǎn)點(diǎn)頭。
“感情”這個(gè)詞兒,楊大成歷來“恕不恭敬”。可是當(dāng)他看見王小清掛著淚珠一笑,不禁眼皮又一澀。不過這種感受,后來一直是珍藏在他心里的秘密。
什么樣的失戀都痛苦
與楊大成不同,梁黑子一開始就喜歡上王小清了。
他倆第一次打交道是為打針。這個(gè)伏牛山區(qū)的小娃子,長(zhǎng)得矮胖矮胖,圓臉圓眼睛圓鼻子頭,臉上經(jīng)常帶著好奇、小心、謙恭的神情。可是針一扎進(jìn)屁股蛋里,他就喊起來了:“好大姐,不敢打呀!”
王小清本來勸他:“不怕不怕,只有一點(diǎn)點(diǎn)痛。”聽他喊自己“大姐”,竟紅了臉,笑得彎下腰,連忙護(hù)住注射器,停止推藥。
她看過他的病歷,知道他比自己大三個(gè)月。自那以后,她倒真對(duì)他擺出一副姐姐的架式了:叫他做個(gè)棉簽打掃個(gè)衛(wèi)生,用的是吩咐的口氣;做他的思想工作,用的是哄勸的口氣;他要是受了別人的委屈,她還要出來保護(hù)保護(hù)。梁黑子有四十幾元錢,大半是參軍時(shí)從家里帶來的。誰知?jiǎng)⒂裰懒耍f要買一雙牛皮鞋,點(diǎn)著名找他借走了三十。為這事兒,梁黑子躲在被子里哭了一晚上。他不敢告訴別人,卻悄悄告訴了王小清。王小清一聽,氣呼呼地找到劉玉:“劉玉,你干什么欺負(fù)人家小梁?”
“這是從哪說起的呀?”劉玉見她就樂。
“不害臊,四年的老兵找人家新兵借錢!”
“這是兩廂情愿的呀,怎么的啦?”
“什么什么?人家不敢不借給你,知不知道!”
“是嗎?可笑!好好,遵命,鄙人馬上送還。”
劉玉把三十元票子朝梁黑子床上一摔,一撇嘴:“傻呼呼的,看不出來,倒學(xué)會(huì)了告刁狀!”
劉玉不但知道梁黑子錢包里有錢,還知道那里面藏著一張姑娘的照片。還錢的事情以后,劉玉就對(duì)梁黑子沒有好臉了。楊大成轉(zhuǎn)入急救室后,有一次劉玉故意當(dāng)著王小清和朱銳的面,似笑非笑地說:“黑子,把你老婆的照片公開公開嘛!”
當(dāng)時(shí)四個(gè)人正圍著一個(gè)臟盆子拔臟棉簽,有說有笑的。聽劉玉一說,大家一楞。梁黑子刷地紅了臉。
劉玉追問道:“你每天中午躲在被窩里看的是什么?”
“哪里……不是……”梁黑子尷尬極了。
“是對(duì)象吧?”朱銳故作好奇,想給他個(gè)臺(tái)階。
梁黑子勉強(qiáng)點(diǎn)點(diǎn)頭。
王小清卻大感好奇,嚷道:“快把照片拿出來看看——?jiǎng)⒂衲闵儆憛挘裁蠢掀爬掀诺模y聽死了。”
“那叫什么?親愛的?”
“親愛的怎么啦?你不要把高尚的字眼說得流里流氣的!小梁,咱們別理他!”
叫王小清一鼓勁,梁黑子漲紅的臉上露出一點(diǎn)兒笑。他伸手在貼身病號(hào)服里掏出錢包,果然抽出半個(gè)巴掌大的一張照片。這是一張鄉(xiāng)間小鎮(zhèn)照相館的作品:反差大,色調(diào)生硬,畫面呆板,一幅亭臺(tái)樓閣的布景,正中立正站著一個(gè)穿方口扁頭土布鞋,胖圓臉,表情由于緊張和害羞顯得呆滯的農(nóng)村姑娘。
“她好象比你大兩歲吧?”王小清怕把照片弄臟了,用兩個(gè)指頭捏著一個(gè)角。
“只大兩個(gè)月。”
朱銳和善地問:“是青梅竹馬?”
“哪,俺倆總共才見過兩回面。”
“包辦婚姻唄!”劉玉說。見梁黑子點(diǎn)點(diǎn)頭,他又一本正經(jīng)地問,“花多少錢啦?”
“七、八百吧。”梁黑子又連忙笑笑。
“那個(gè)每次都把六五一醫(yī)院寫成六五一部隊(duì)的,八成就是這位親愛的吧?”
梁黑子緊張了,望著劉玉“嘿嘿”傻笑。
王小清糊涂了,連問:“怎么回事?”
“怎么回事?他怕那位親愛的知道他得了肺結(jié)核,不跟他,錢也白花了,就給人家寫假地址唄。反正大地名沒寫錯(cuò),郵局試投也能收到。”
朱銳皺起眉頭問梁黑子:“真的?”梁黑子只是乞求地咧咧嘴。朱銳說:“你這樣做恐怕就不對(duì)了。”
王小清又搖腦袋又?jǐn)[手,說:“算了算了,不就是把地址寫錯(cuò)了嗎?有什么了不起的!”
朱銳說:“為人要忠誠老實(shí),何況是對(duì)終身伴侶!”
劉玉也幫腔:“就是嘛,就是嘛。”
王小清不對(duì)朱銳,卻對(duì)著劉玉嚷嚷:“什么呀什么呀,人家生了病,怕家里掛念,有什么不對(duì)的?”
“你倒會(huì)替他找臺(tái)階。”劉玉說,“問問他自己嘛,到底是怕人家掛念還是怕丟了老婆?”
梁黑子的腦袋耷拉下來,抬不起來了。
王小清又嚷嚷:“就算是又怎么樣?得了肺結(jié)核就希望別人都快點(diǎn)把你們甩啦?”
劉玉忙擠擠眼睛說:“好好好,姑娘們要都象你這么想,我們還有什么后顧之憂!”
朱銳卻認(rèn)真地說:“王護(hù)士的好心,我倒是可以理解。但是這對(duì)我們有多大幫助呢?得了肺結(jié)核,我們?cè)谌松牡缆飞辖涣硕蜻\(yùn),這就是我們面對(duì)的殘酷現(xiàn)實(shí)。難道靠哄,靠騙,就解決問題了嗎?我們怕復(fù)員,怕退學(xué),怕把對(duì)象吹了。可怕有什么用?我說跟別人比起來,我們?cè)谌松牡缆飞隙嗔艘坏揽部溃嗔艘淮五N煉和考驗(yàn)。在這種意義上說,咱們真是幸運(yùn)呢!”
王小清大受感動(dòng):“這就是你在可能會(huì)退學(xué)、會(huì)退役的情況下,還每天堅(jiān)持學(xué)數(shù)理化的想法?”
“對(duì)。”朱銳莊重地說,“我準(zhǔn)備再考理工科。”
梁黑子突然抬起頭,拖著哭腔說:“就俺是個(gè)孬種啦!您請(qǐng)都放心,俺明天就給她寫信承認(rèn)錯(cuò)誤,今兒黑了就寫!”說完就嗚嗚哭起來。
“別哭。”王小清忙制止他,“還是個(gè)男子漢呢!”
可是過了半個(gè)月,梁黑子又哭了,而且哭得極傷心。他寄出了“承認(rèn)錯(cuò)誤”的信以后,遲遲不見女方回信,終日愁眉苦臉。王小清嘴上不說,心里也捏了一把汗。后來梁黑子的哥哥來了信,說女方家里得知他得了“癆病”,退了婚也退了禮。對(duì)他的悲傷,朱銳覺得滑稽可笑:“不了解就談不上愛情,沒有愛情又有什么必要如此傷心呢?”劉玉則跑去報(bào)告王小清,“哎,你弟弟的高尚愛情完蛋了,正在無限痛苦呢1”
王小清翻他一眼:“你這個(gè)人呀,為什么別人痛苦了,你就高興呢?”
“別人有的我都要”
梁黑子丟了未婚妻,情緒低落。劉玉卻更警覺了。因?yàn)樗l(fā)現(xiàn)這個(gè)小新兵蛋子跟王小清更近乎了。“還真有想吃天鵝肉的?”他悄悄地監(jiān)視起兩個(gè)人來。
那天下午,朱銳帶著外語書,跑到外面不知哪棵樹下啃去了。楊大成剛從急救室轉(zhuǎn)回來,躺在床上睡覺。梁黑子坐在床邊小凳子上埋頭傷心。劉玉算準(zhǔn)了王小清要來找梁黑子,就躺在床上裝睡。果然她來了。只聽她往梁黑子床上一坐,壓低聲音問:“小梁,不要遇到一點(diǎn)挫折就這個(gè)樣子嘛!”
“俺現(xiàn)在想啥都沒心,俺覺得活得沒勁。”
“你呀!對(duì)象吹了就活得沒勁了?還不如我!”
“俺誰都不如,誰都瞧不起俺。”
“討厭,誰瞧不起你啦!我是說你該學(xué)學(xué)朱銳。”
梁黑子不吭氣了。王小清又噗嗤一笑說:“其實(shí)呀,我也不行。我剛穿上軍裝時(shí),也想象過堵槍眼呀,救火車呀,要當(dāng)一個(gè)真正的雷鋒呀。可連想家都克服不了。到現(xiàn)在還想媽媽,想吃她炒的硬蠶豆……
“你猜我最怕什么?癩蛤蟆。剛到軍醫(yī)學(xué)校,新學(xué)員都參加勞動(dòng),蓋新教學(xué)樓。清理地基,開頭我干勁可大了,后來石頭里蹦出來個(gè)癩蛤蟆,嚇得我一整天就站在邊上看別人干,說什么也不干了。結(jié)果晚上專門開我的班務(wù)會(huì)呀!班長(zhǎng)說:‘啊,一不怕苦二不伯死,碰到個(gè)癩蛤蟆就不要組織紀(jì)律,不要完成任務(wù)啦?偏要我作檢討。我哭啦,我說,‘哼,我一不怕苦二不怕死,就是怕癩蛤蟆!……”
梁黑子“哼哼”地笑了。
“我特別怕晚上一人呆在外面。在軍醫(yī)學(xué)校的時(shí)候,我們短期下連當(dāng)兵,在一個(gè)勞改農(nóng)場(chǎng)搞守衛(wèi)。本來女同志都是雙哨,有一天不知怎么,半夜叫我一個(gè)人上了一班哨!哨位在一片樹林子里,那天晚上有風(fēng),樹葉兒亂響呀!還有云,半個(gè)月亮呀,一會(huì)兒遮黑了,一會(huì)兒又亮了,真害怕呀!我聽到有個(gè)聲音,‘啪嗒啪嗒,從小路跑過來啦。我端起半自動(dòng)步槍,使勁喊:‘誰?聲音停了。我更怕了呀:‘誰?不說話我就開槍啦!結(jié)果你看,真走出一個(gè)男的來。我問:‘你是誰?他說:‘我是那邊生產(chǎn)隊(duì)喂牛的,牛丟了,隊(duì)長(zhǎng)叫我出來找。我一聽,放心了,說:‘好,你去吧。,他連忙說:‘謝謝,謝謝!跑了。
“過一會(huì)兒,‘啪嗒啪嗒又響起來了!我嚇得要命,端起槍喊:‘誰,再不站住我開槍啦!就看見幾個(gè)黑影一下躲到樹后邊去了。我想,這下子壞人真的來啦。反正遇到緊急情況可以開槍,我的子彈又是早就上了膛的,我對(duì)著他們使勁一扣扳機(jī)。不知怎么扣不動(dòng)!我差點(diǎn)兒癱在坑里……結(jié)果,他們包圍了我,一把奪走了我的槍。原來是一個(gè)副連長(zhǎng)和兩個(gè)戰(zhàn)士。副連長(zhǎng)沖我吼:‘你搞的什么名堂,怎么不問口令?他把我的槍嘩啦嘩啦扳兩下,又說:‘哼哼,幸虧忘了打開保險(xiǎn),要不然還把我們槍斃了呢!”
“頭起跑的那個(gè)呢r”梁黑子興致勃勃起來。
“就是啊,那才真是個(gè)越獄的勞改犯,副連長(zhǎng)他們就是去追他的!”
“嗬嗬嗬,勞改犯叫你給放了,追他的倒差點(diǎn)給你崩了,嗬啊嗬……”剛醒的楊大成嗡嗡說。
王小清補(bǔ)充說:“不過那個(gè)犯人天不亮就給捉回來了。農(nóng)場(chǎng)周圍幾十里都是‘網(wǎng),誰也跑不掉的。”
過了一會(huì),梁黑子嘆口氣,誠懇地說:“王護(hù)士,俺喊過您大姐,叫人笑話了。俺倒覺著你象俺娘!”
“呀,討厭,你怎么瞎打比方!”
“當(dāng)真哩,俺遇著傷心的事了,俺娘就是這樣,給俺講笑話啦,講故事啦,讓俺寬心。”
劉玉聽到這兒,對(duì)梁黑子也寬了心。如果一個(gè)小子想求愛,哪有管姑娘叫娘的!他望著王小清發(fā)愣。不知什么時(shí)候起,她的一切一切,與日俱增地刺激著他的幻想。終于在一天熄燈的時(shí)候,他向全室成員鄭重宣布:他已經(jīng)向王小清送交了“第一封情書”。
三個(gè)人都很震驚。梁黑子用眼睛翻他,楊大成眼睛里燃起了怒火。
“你真的愛她嗎?”朱銳問。
“要不我把情書底稿公開念一念?”
“胡來!”楊大成拉開被子上床。
“這件事你是認(rèn)真考慮的?”朱銳又問。
“伙計(jì),別以為只有你們啃了兩本書的會(huì)動(dòng)腦筋,咱什么問題都認(rèn)真考慮。怎么的?”
“那你找她,你認(rèn)為合適嗎?”
“你說咱配不上?嘿嘿!”他挑釁地掃視大家,“論家庭條件,咱是工人子弟,她也不是什么高干子女,爹媽是縣中學(xué)教師。論本人條件,她當(dāng)護(hù)士,干部里頭最小的。咱復(fù)員回家當(dāng)工人,工資帶獎(jiǎng)金,比她拿得多。比不上她的,就是個(gè)身體唄。可咱聽說她也有什么病!”
劉玉把王小清的情況摸得這么清,出乎大家意料。說王小清有病,更叫大家吃驚。大家沉默著。
“所以咱就想開了,至少我自己不歧視自己!”劉玉揚(yáng)起了眉毛,“你要看咱矮一頭,咱偏要比你高一頭!咱活一天,就要痛痛快快把這一天玩得美美的!別人有的我都要!怎么的,咱就這樣!”
“問題是怎么樣才叫活得美。”朱銳說。
“別賣弄啦,說幾句大道理,你就當(dāng)上指導(dǎo)員啦?你常愛用‘意義,梁黑子天天做好事,有意義吧?他可會(huì)寫假信騙取婚姻呢!咱這直截了當(dāng)?shù)模谝徊骄透夜_情書,怎么的,倒沒‘意義了?”
朱銳懶得跟他辯了。梁黑子象挨了當(dāng)頭一棒,又蔫了。楊大成不耐煩地翻個(gè)身,連讀“關(guān)燈”。
第二天,當(dāng)王小清推車進(jìn)來發(fā)藥的時(shí)候,屋里空氣緊張起來,四雙眼睛都跟著她。她低頭戴著大口罩,對(duì)誰都不敢看,把藥杯擺在每個(gè)人床頭,轉(zhuǎn)身就走。臨出門,回頭低聲招呼:“小梁,你出來一下。”
梁黑子象屁股上有根彈簧,蹦起來跟著出去了。不到兩分鐘,他回來了,盡量想表現(xiàn)得若無其事,胖臉蛋卻忍不住放出光來。他把一張迭得小小的紙條交給劉玉說:“王護(hù)士叫還給你哩。還叫告訴你,再寫這玩意兒,她就交給護(hù)士長(zhǎng)了!”
劉玉臉上的肌肉僵硬了。他首先意識(shí)到丟了丑。但過一會(huì)兒,他卻又自嘲地淡淡一笑:“戀愛自由嘛,何必搞得這么可怕!小題大作,可笑可笑1”
當(dāng)著大家的面,他隨隨便便地把情書撕碎了。
不怕死
自打從急救室出來,大家都說楊大成變了,變得消瘦了,和善了,不抽煙了,配合治療了,有時(shí)還獨(dú)個(gè)兒哼哼唱唱的。這天上午,風(fēng)和日麗,王小清來接班,遠(yuǎn)遠(yuǎn)見他坐在小溪邊一塊石頭上,好象在望著溪水發(fā)呆。走到他背后了,才聽見他在唱歌。他反復(fù)唱的是這么幾句詞兒:“唱吧朋友們,明天要航行,航行在那夜霧中。快樂地歌唱吧,親愛的老船長(zhǎng),讓我們一起來歌唱。”他唱得很輕,音調(diào)也不準(zhǔn),但嗓音很渾厚,流露著深沉的回憶和向往。覺察到身后有人,他回頭一看是王小清,不唱了。
“呀,想不到你唱得這么動(dòng)人。你唱呀!”
“嗬嗬。”楊大成搓搓手。
王小清笑了,十分快活。楊大成看她:軍裝襯出了纖細(xì)的身段,剛洗過頭,軍帽拿著,半干的頭發(fā)用一塊花手帕系在腦后,象山石中涌出的烏亮的泉水。那雙黑眼睛亮亮的,甜甜的。“講點(diǎn)你們海軍的事兒吧!”她突然要求,在另一塊石頭上坐下來。
“那有什么好講的。”
“呀,隨便講一點(diǎn)唄,我可孤陋寡聞啦!”王小清一噘嘴。“那就講唱歌?”楊大成問。
“講什么都行。”
“我們不唱歌,干啥呢?第二天要出遠(yuǎn)海,頭天晚飯后能上岸的不上了,都上甲板了。也沒入起頭,也沒人指揮,都唱啊!”
“海上生活枯燥?”
“你說呢?除了天就是海,除了海就是天,艙又小,幾十天,一兩個(gè)月。你說呢?”
“那你們不喜歡大海?”
“不喜歡?”他瞪起了眼睛,但立刻又柔和下來。他嘆了口氣,“以后完啦,回不去啦!”
王小清知道勾起了楊大成的傷心事,沉默了一陣,說:“在哪兒不一樣嗎?你不喜歡陸地?”
楊大成笑笑,看著她,象看一個(gè)不懂事的孩子:“經(jīng)常遠(yuǎn)離呀,有誰能比我們更喜歡陸地!”
“那不就行啦?”
“沒那么簡(jiǎn)單喲!”
“哼,”王小清突然一撇嘴,“沒看出來,你的感情還真豐富!我以為你就會(huì)發(fā)脾氣呢!”
“你記仇,就不好了。”楊大成低下了頭。
王小清笑了:“我記你的仇干啥呀?不配合治療,倒霉的不是你自己?jiǎn)幔俊?/p>
楊大成松了一口氣,又忽然想起來說:“朱銳呀,學(xué)我耍混,你得過問過問了。”
原來,醫(yī)生告訴朱銳,他肺部空洞較多,要做肺切除手術(shù)。于是他就一百八十度大轉(zhuǎn)彎,不吃藥,還開始學(xué)抽煙。王小清聽了不相信,跟楊大成一起回到樓里,她匆匆換上工作服,提著體溫欄就去查體溫。進(jìn)了病室,果然見朱銳靠墻坐在床上,手指間正夾著一支煙。王小清呆望了他一陣,哀求似地說:“不要這樣好吧,朱銳。”
“不要什么呀?”朱銳表示奇怪。
“不要這樣好不好,你的意志那么堅(jiān)強(qiáng)的呢!”
“我的意志并沒有絲毫衰退呀!”
“……那你不吃藥,還抽煙。”
“沒那么嚴(yán)重。”朱銳吸一口煙,猛咳起來,嗆出了眼淚,“你知道歐米埃爾嗎?”
王小清搖搖頭。
“歐米埃爾曾是個(gè)美麗得出名的姑娘,后來衰老得丑陋無比。雕塑大師羅丹就雕塑了這么個(gè)丑老太婆。結(jié)果呢,比美麗更加震驚世界。懂這個(gè)意思嗎?”
王小清又搖搖頭。
“美麗的東西也會(huì)衰亡。這就是羅丹說的真理。我們何不在丑陋和衰亡到來之前就結(jié)束呢?好戲都在高潮收?qǐng)龅摹!?/p>
“你瞎說什么呀!你平常不是這樣說的!”
“你錯(cuò)了。我平常說的跟這個(gè)不矛盾。我住院第一天就這么準(zhǔn)備了,生病之前就這樣計(jì)劃人生了。”
“不怕死,是吧?”劉玉插上一句,“好樣兒的嘛!”
朱銳釋然一笑說:“王護(hù)士你放心,我沒事兒,真的,保證配合治療。”
王小清被弄糊涂了,也沒詞兒了,只好給大家發(fā)體溫計(jì)。發(fā)到劉玉面前,她又低下頭。劉玉突然指著她的工作服說:“哎,王護(hù)士,你的兜怎么濕啦?”
王小清這才發(fā)現(xiàn),工作服左兜濕漉漉的。她伸手進(jìn)去,摸到一個(gè)涼冰冰、軟綿綿的東西,臉就嚇黃了;猛地拎出來甩到地上,竟是一只大癩蛤蟆。嚇得她尖叫一聲,木制的體溫欄“砰”地摔到地上,十幾支體溫計(jì)蹦出來,全摔碎了。
癩蛤蟆是劉玉放的,可是他沒想到會(huì)鬧出這么個(gè)結(jié)果。十幾支體溫計(jì)呀!王小清的淚水在眼睛里打轉(zhuǎn)兒,不知所措地連連說:“看你,這可怎么辦……”
梁黑子下了地,默默地?fù)炱痼w溫欄,遞給王小清。她接過來,忍著抽泣,轉(zhuǎn)身跑出去了。梁黑子蹲下,抓起那只癩蛤蟆。這個(gè)素來怕劉玉的新兵站起來,兩眼直逼劉玉。劉玉也緊張起來。這時(shí),楊大成卻發(fā)話了:“小梁,把癩蛤蟆扔出去!”
梁黑子沒反應(yīng)。楊大成下床,一只手拍到他肩上。梁黑子掙了兩下沒掙脫,癩蛤蟆在他手里被捏得四腳亂彈。楊大成沖著劉玉說:“你運(yùn)氣!要不是如今,哼,我就背個(gè)處分!”
劉玉心里發(fā)怵,臉上卻不在乎地一笑:“想揍我呀?來吧!挨了揍再叫醫(yī)院開除我,都行!沒地方治了就是個(gè)死吧,怎么的,咱也跟朱銳一樣,不怕死!”
“跟我一樣?”朱銳嗤地一笑,“可憐1”
“我愛……”
親愛的黑子同志:
您好吧!您一定還在生俺的氣吧?自從上次您來信說住院了,俺娘就要退婚。俺不答應(yīng),她就說俺爹就是死在“癆病”上的。俺哭了幾天也不管用。前天你們醫(yī)院來了信,開口管俺叫姐,管自己叫妹妹。她說現(xiàn)在“癆病”能治好;還說您因?yàn)橥嘶椋y過死了,說明您對(duì)俺好是真心;還說現(xiàn)在青年人戀愛,就是要忠誠;還批評(píng)俺這時(shí)候離開您,對(duì)您身體可不好。俺邊看邊掉淚,就念給俺娘聽,她聽著也點(diǎn)頭嘆氣,可過后還是不答應(yīng),氣得俺又跟她吵一架!
您放心,俺寫了這封信,就是要您告訴俺那不知名的好妹妹,俺和您這輩子好到老,海枯石爛不變心。反正婚姻自主,俺啥也不怕……
梁黑子眉飛色舞地念,楊大成和朱銳拍巴掌喊好。還沒念完,朱銳說:“我說小梁啊,前一段你們訂婚倒沒什么愛情,這么一退婚反而把愛情給找來啦!”
楊大成說:“你們猜,寫信的是誰?”
梁黑子說:“王護(hù)士唄,旁人誰知道地址!”
朱銳說:“主要是只有她的心這么好。這信得給她看看,可她怎么還沒上班呢?”
“她就是這一班,怎么沒來就不知道了。”一直置身局外的劉玉突然插話了。癩蛤蟆事件后,他本以為科里會(huì)狠狠整他一頓,打算破罐子破摔,硬著頭皮頂?shù)降住2涣系鹊降诙煲矝]見動(dòng)靜。他向楊大成打聽,楊大成沒好氣地告訴他:“人家王護(hù)士兜著了,掏錢賠啦!”“要她掏什么錢?”“她說是她打碎的唄,記她的差錯(cuò)唄,等著全院點(diǎn)名唄!”“我不用她來這一套!”“你,你還想叫她挨批呀?”“我去承認(rèn),還叫她挨什么批?”“批她欺騙領(lǐng)導(dǎo),包庇壞人壞事!”“我好漢做事好漢當(dāng),她為啥包庇我?”“說你有病,怕你吃虧唄!”
這時(shí),經(jīng)朱銳一提,劉玉的心里象被戳了一下:“我問問去,她為什么沒來上班。”
誰也沒料想,他出去一會(huì)兒,就慌慌張張跑回來,帶來了一個(gè)爆炸性的消息:“她病啦!很重的病!”
劉玉曾聽說過王小清有病,這病叫“慢性粒細(xì)胞性白血病”。但他不知道,這就是“血癌”。王小清是剛從學(xué)校分到這所醫(yī)院,就被發(fā)現(xiàn)確診的。送到軍區(qū)總醫(yī)院住了兩個(gè)月院。這種病極難根治,只要病情穩(wěn)定了,就可以延續(xù)生命。于是她堅(jiān)決要求出院投入工作,還要求對(duì)病號(hào)們,甚至盡可能對(duì)工作人員保密,使大家象對(duì)待常人那樣對(duì)待她。不答應(yīng)她是不可能的,醫(yī)院只好讓她邊工作邊治療。而這一次她突然病倒,屬于慢性白血病的急性病變,可以說是最后時(shí)刻到了。
四個(gè)病友都傻了,半天才決定馬上去看她。
六五一結(jié)核病院有近三百張結(jié)核病床,卻只有三十幾張普通病床,很好找。但結(jié)核病號(hào)當(dāng)然不能往那里去。四個(gè)病友利用治療后到午飯前的空隙溜出去,很快找到了王小清的病室。但里面的人太多,他們沒法進(jìn)去,只好從窗外的簾縫往里看。
那是一個(gè)單人急救室。她仰面躺著,陷進(jìn)軟褥子里,被子蓋在瘦小的身軀上,顯得癟癟的。她的臉色蒼白而且泛黃,兩個(gè)鼻孔塞上了棉花,顯然是剛出過血。她顯得疲乏,喘氣好象很費(fèi)力。
看見了她,四個(gè)病友很難過,好象終于相信了某個(gè)可怕的事實(shí)。睡午覺時(shí),他們又溜去了。這次很順利,看望她的人和醫(yī)生都走了。“睡著了,就不準(zhǔn)出聲,看看就走。”進(jìn)門以前,楊大成下了命令。
王小清閉著眼,鼻孔里的棉花已經(jīng)拿掉,一縷汗?jié)竦念^發(fā)斜著貼在蒼白的額頭上,使她顯得神態(tài)安恬。四個(gè)人輕手輕腳走進(jìn)來,剛在她床邊站定,她就睜開了眼睛:“你們……你們?cè)趺床艁硌剑俊?/p>
有一陣,大家都不知怎么安慰她才好。
“王……俺姐,你好嗎?”梁黑子問。
“痛啊,”王小清笑笑,“胸部一壓就痛,四肢關(guān)節(jié)痛得象刀攪。典型癥狀。”
又沉默了一陣。王小清眼睛轉(zhuǎn)向天花板,終于說:“我原來以為至少還有五、六年的時(shí)間,沒想到會(huì)這么快。一般應(yīng)該有五、六年左右的呀!”
朱銳忙說:“別傷心,你第一次都好了,這次也會(huì)好的。”他想笑笑,可臉上肌肉不聽話,沒有笑成。
“我不如你,”王小清看著朱銳,淚珠兒終于滾了出來,“自從得了這個(gè)病,我就常常難過,晚上偷偷地哭。我才十八歲,比小梁還小……”
一陣感情的震顫滾過四個(gè)男子漢心頭,大家都不敢看她了。
“活著,多有意思呵!”王小清悲哀的眼中閃出一絲神往的光。她象自語似地說:“我護(hù)理過的病號(hào),好了,出院了,高高興興的……有的專門來跟我告別,有的臨走忘記了,還有的因?yàn)樯业臍猓詈笠膊焕砦摇嘤幸馑及。晌遥覟槭裁匆馈彼槠饋怼?/p>
朱銳突然沖動(dòng)起來,兩手在胸前亂摸:“別,別……我不想死了,我交給你……”他從衣袋里掏出個(gè)小藥瓶,眼淚亂流,“這是毒藥,是我住院前偷偷準(zhǔn)備的……我還自以為是,其實(shí)我算什么東西呀!”
“低聲點(diǎn)!”楊大成低聲吼他。
他拿著個(gè)小藥瓶,手在發(fā)抖。王小清對(duì)他嘆了口氣說:“你會(huì)好的,其實(shí)你把手術(shù)看得太可怕了。我們年年都有手術(shù)以后痊愈出院的。”她又象想起了什么,把眼光落在劉玉身上,“劉玉!”她親切地叫他。
“嗯。”劉玉站在床腳,心神不寧地低著頭。
“你來。”
劉玉不敢抬頭,往前挪了一步。
“你來呀,到我床頭邊上來。”王小清聲音微弱地說,“別生我的氣吧,劉玉。”
“不……不……”
“不要生我的氣。我是說你寫的那個(gè)信。我還小,不知道怎么談戀愛,我害怕,而且我還有病。我……我沒有權(quán)力害別人……”王小清又哽咽起來,“我……我本來想好好跟你講清楚,可,可又怕講不清。我不該用那種方法刺激你,可我又怕你再寫……”
“我……不……”劉玉突然轉(zhuǎn)身推開三個(gè)病友,沖出門外,一屁股蹲在走廊里,放聲號(hào)啕起來。一邊哭,一邊沒頭沒臉重重地打著自己……
他驚動(dòng)了值班護(hù)士……
兩天以后,舉行了向遺體告別儀式。
從禮堂那邊傳來了隱隱約約的哀樂聲,從陽臺(tái)外邊傳來了淙淙的溪流聲。
很久,他們才開口說話。
“俺的那封信,到底沒能念給她聽!”梁黑子一張口,眼睛就濕潤了。
“她留戀生命,因?yàn)樗龕蹌e人,她沒有絕望。而我不怕死,因?yàn)槲易运剑医^望了!我膽小,我真渺小啊!”朱銳似乎在夢(mèng)囈。
楊大成默默站著,把手指捏得嘎吱吱響。
劉玉哺喃地說:“她怕癩蛤蟆……我連個(gè)對(duì)不起都沒顧得說……”他突然想起什么,對(duì)大家說,“她害怕晚上一個(gè)人呆在外面!”
三個(gè)病友都愣愣地望著他。
“晚上,她在太平間,咱們?nèi)ヅ闼 彼啊?/p>