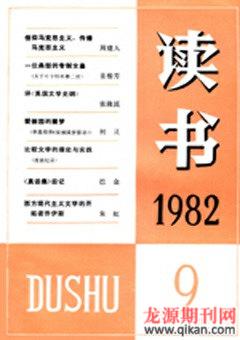格姆科夫《我們的一生》
盛 博
恩格斯晚年曾經自豪地說過:“我們的一生沒有虛度”。這句樸素的話,恰如其分地概括了馬克思恩格斯兩位無產階級革命導師的一生。東德的馬克思主義史專家格姆科夫取意于恩格斯的這句話,以《我們的一生》為題,寫了一部給青年人看的馬克思恩格斯傳記。
中國讀者對海·格姆科夫(HeinrichGemkow)并不陌生。三聯書店在七十年代末連續出過他的兩本傳記:《馬克思傳》《恩格斯傳》。馬恩傳記解放后雖然譯過不少,但這兩本還是能給讀者以深刻印象。因為象梅林的《馬克思傳》不免嫌陳舊一些,科爾紐的幾大卷《馬克思恩格斯傳》又過于瑣細;而無論就觀點或材料來說,格姆科夫的書都較過去斯捷班諾娃的《恩格斯傳》稍勝一籌。因此,中譯本出版以后曾經一再重印,不無原因。
這部《我們的一生》譯為中文約二十萬字,前述格姆科夫的兩部書有一百萬多字。原先以為,這本書無非是從那兩本書中節略而成,是一種“壓縮餅干”。翻閱之下,覺得并不。《我們的一生》還是有其特色,值得一提。
東德大學生的報紙《論壇報》在今年第二期上登載了一篇《格姆科夫教授為馬克思恩格斯的新傳記答本刊記者問》,格姆科夫在談話中介紹了自己的這部新著。他認為,把馬克思和恩格斯的生平合寫成一本正式的通俗傳記,是他“首創的新嘗試”。要是說過去從沒有人寫過馬恩合傳,不免是夸大之辭,但如果說這本書在這一點上有其特色,也許不無道理。事實上,馬克思和恩格斯無論在思想、事業、信仰上都是密不可分的。資產階級的所謂馬克思學專家曾經企圖把他們兩位的思想生硬地劃分,甚至說恩格斯“背叛”馬克思的某些思想,那是胡謅。當然,對于專業工作者來說,準確地分別敘述兩人的業績也有其一定必要,但是對青年讀者來說,把馬恩生平合在一起作為一個整體敘述可能更好一些。有些地方比較難以合寫。例如早年的活動,馬克思在特利爾,恩格斯在巴門,各自生活,彼此還不認識,如何合寫?但作者以《萊因省的兩個資產階級兒子》為題,頗為巧妙地交待了他們兩人當時在地區、時代、出身等方面的共同之處。當然,馬恩的家庭環境、早年生活在某些方面出入是很大的,這些對青年讀者不去詳細比較我看也無可厚非。
這本書另一可取之處是敘述比較生動。寫馬恩傳記,往往容易枯燥地介紹思想,單純論述馬恩學說要點。這樣做,有時使得一本馬恩傳記同馬克思主義發展史看不出多少區別。其實傳記主要還是寫人,不論這位傳主是偉人還是普通人。這本給青年看的傳記,重點在寫馬恩斗爭、工作、生活中的事,特別是足以說明他們生平特征的軼事。這是可取的。當然軼事要選取得當,不能流于庸俗。書中開頭從介紹馬克思的那篇關于選擇職業的著名作文入手,襯托出中學生時代的馬克思,就頗為成功。作者在引述了作文中的結語后說:“這是多么富有詩意的語言!盡管今天讀起來,或許略有語言雕琢之感。但我們應該考慮到,那是講究華麗纖巧的文體和浪漫派文學接近尾聲的時代。然而文章的思想是大膽地脫俗!誠然,作文的內容帶有當年時代的理想——德國古典哲學和文學中的人本主義的烙印。要知道,這時離歌德寫下他的詩篇《神性》才只有幾十年的功夫,歌德這首詩的最初幾行是:‘人應該是高尚、樂于助人、善良……而離《浮士德》第二部的完成和發表才只有四年時間呢!”這種分析和寫法,看來完全可以接受。它并沒有把中學生的馬克思寫成不世的天才,說明馬克思也確實受時代的限制,然而又寫出了馬克思畢竟那么的不凡!
要寫生平,就免不了寫到私人生活。書中寫馬克思的愛情生活,他的清貧,馬恩的友誼,直至寫馬克思的女兒們如何“踏著父親的足跡”,都有可觀之處。寫恩格斯同愛爾蘭女工瑪麗·白恩士的共同生活時說:“她是他深情鐘愛的女人,既是戰友,又是生活伴侶。……當時占統治地位的倫理規范禁止他們公開結合。一個工廠主的兒子和一個工廠女工結婚是不可思議的。于是只有一個辦法:公然蔑視資產階級的道德風尚——他和瑪麗非正式同居,直到一八六三年一月七日瑪麗去世。”這種論述,不背于事實也不流于庸俗。從一個中國讀者角度說,也許會覺得有些問題不必強調得那么多。例如在敘述十九世紀末、二十世紀初恩格斯的活動時,突出地渲染裁軍和“工人階級需要和平”。從這里,倒使我們明顯地感到我們非常需要有中國作家寫的馬恩生平傳記,要有各式各樣自己創作的耐讀的有關書籍。我想,只要重視起來,當是不難做到的。
作為引進和借鑒,聽說天津人民出版社已在組織翻譯這本書。這很好,我們期待它的問世。
(UnserLeben.EineBiographieüberKarlMarxundFriedrichEngelsvonHeinrichGemk-ow.DietzVerlag.Berlin.1981.334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