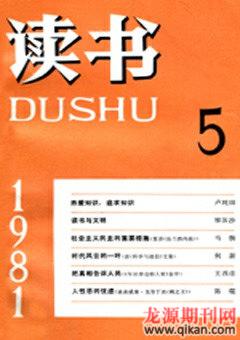文學(xué)中的預(yù)言
封 葦
據(jù)說,文學(xué)評(píng)論中有一種叫做“印象派評(píng)論”,那么這篇拙作就算是這種體裁的模仿吧。因?yàn)椋瑥執(zhí)煲硗镜摹堆鬀茕浩鎮(zhèn)b》我手頭既沒有;這部小說在三十年代的《現(xiàn)代》月刊上連載后有沒有出過單行本,甚至小說是否寫完,我都忘記了。但小說給我的印象甚深,我常常想到它,近來更由于許多原因,還想談?wù)勊?/p>
《洋涇浜奇?zhèn)b》發(fā)表的那個(gè)時(shí)代,報(bào)紙上常可以看到年輕人逃出家庭,離鄉(xiāng)背井,要到峨嵋山之類的名山去訪道求仙找劍俠的新聞。張?zhí)煲硗緦戇@本小說的用意,我當(dāng)時(shí)想,當(dāng)然是通過寫一,部二十世紀(jì)的中國(guó)《唐·吉訶德》,諷刺武俠小說迷的辦法,來描寫舊中國(guó)的混亂和某些階層的愚昧吧。小說寫得很生動(dòng)有趣,主要描寫的是一個(gè)上了武俠小說的當(dāng),真想成劍俠的、不懂事的第三流公子哥兒,幾個(gè)騙子手,另外是周圍一些不三不四的男女。
這個(gè)題材本身就非常妙,與作者所擅長(zhǎng)的拉布雷式“謔而近虐”的筆調(diào)相得益彰,使我至今認(rèn)為這是中國(guó)新文學(xué)中一部不同凡,響的,也可說是突破框框的作品。但不知為什么,后來很少為人提及。不管是為什么吧,我覺得這不但有欠公允,并且還埋沒了這部小說所包含的另一種重大意義。
這部小說很深刻地描寫了當(dāng)時(shí)現(xiàn)實(shí)中很少人注意的一個(gè)側(cè)面;而且,正因?yàn)槊舾械刈阶×爽F(xiàn)實(shí)中的那些現(xiàn)象,還具有“預(yù)言”的性質(zhì)。
我這句話,并非溢美之詞,而是因?yàn)槲矣杏H身的感受。
解放前夕,遍及蔣管區(qū)各地,從大城市一直到窮鄉(xiāng)僻壤,特別是曾經(jīng)敵偽盤踞的地方,各種反動(dòng)會(huì)道門的罪惡活動(dòng)十分猖獗,實(shí)際上成為一支反革命的別動(dòng)隊(duì)。在四十年代后期會(huì)道門最為活躍的時(shí)候,有一次我由于好奇,走進(jìn)一處離我住處不遠(yuǎn)的道壇去看了一看。這個(gè)道壇占了一幢相當(dāng)大的洋樓,外面掛著“某某教上海分會(huì)”的大招牌,香火很盛,善男信女川流不息。當(dāng)時(shí),我還遠(yuǎn)遠(yuǎn)沒有了解這種會(huì)道門的性質(zhì),只是把它看作是騙錢的勾當(dāng)。我進(jìn)去想看的,也只是想看看他們?cè)鯓有序_而已。
進(jìn)去一看,大廳里陳設(shè)得富麗豪華,善男信女們的虔誠(chéng)表現(xiàn),整個(gè)氣氛令人產(chǎn)生一種不愉快的壓迫感。這些都還在其次,最使我吃驚,也是給了我一種深刻啟發(fā)的是:道壇上正在作法的那個(gè)滿臉橫肉、一股殺氣、留著長(zhǎng)須、道士打扮的所謂“仙師”,卻是一個(gè)我認(rèn)識(shí)的人。這人我十年前曾在一位好客的辦報(bào)的朋友那里見過幾次。那時(shí)他還只二十多歲,說是曾找某名山的一個(gè)老和尚為師,還拿出老和尚的六寸大的相片給人看;他說他是訪師學(xué)道、“結(jié)交天下豪杰”到上海來的。不知他通過什么人的介紹到了我那位朋友的小報(bào)館里當(dāng)食客,那顯然是找錯(cuò)了門路,后來就不知去向了。當(dāng)時(shí)的上海灘上,什么人都有,事后我全不把這事放在心上,更不想一想是個(gè)什么問題,連這人的來歷底細(xì)我也沒有打聽。萬萬想不到,十年之后他又竄到上海,并且以這樣的面貌出現(xiàn);這真使我大開眼界,對(duì)事情多了一層深刻的新看法:這一切真不象是二十世紀(jì)在上海發(fā)生的事,倒象是回到了《儒林外史》的時(shí)代;古老的中國(guó)封建社會(huì)在那時(shí)真不只是未散的陰魂,而是有血有肉、活生生的現(xiàn)實(shí)。
看見這位“仙師”,我也就立刻聯(lián)想到《洋涇浜奇?zhèn)b》里的人物。所以,我要說《洋涇浜奇?zhèn)b》是一部預(yù)言性的小說。它預(yù)示了整個(gè)愚昧落后因而反動(dòng)的封建主義還遠(yuǎn)遠(yuǎn)不是一只死老虎,它還要披上各種不同戲裝,在歷史舞臺(tái)上出場(chǎng)表演。
文學(xué)作品作為“預(yù)言”在某種事件發(fā)生前若干年就敏感地描述了事件的萌芽,在世界文學(xué)史上屢見不鮮,可以找到許多例子。詩人和作家不是象海燕一樣能預(yù)示暴風(fēng)雨的來臨嗎?他們常常預(yù)言為人引頸期望的革命;他們有時(shí)也預(yù)報(bào)災(zāi)禍的來臨。預(yù)報(bào)災(zāi)禍正是作家的神圣責(zé)任,這可以使人知道避免它。人總是為了將來而生存著的。
在文學(xué)史上最著名的預(yù)言小說之一,是陀斯妥也夫斯基在一八五九年剛從流放地回彼得堡后寫的一個(gè)中篇《斯捷潘切科沃莊和其中的人物》(這是陀氏最好的作品之一,有些批評(píng)家甚至把這部作品置于幾部長(zhǎng)篇小說之上;但似乎尚無中譯本)。如果有一個(gè)人完全不知道陀氏的生卒年份,看了這個(gè)中篇,多半會(huì)認(rèn)為小說中的福馬·福米奇·奧庇斯金的模特兒就是“人妖”拉斯普丁——在俄國(guó)最后一個(gè)沙皇尼古拉二世宮廷中得寵的、披著宗教外衣的、罪惡累累的大騙子、大權(quán)奸。實(shí)則陀斯妥也夫斯基寫成這本小說的時(shí)候拉普斯丁還未出生,離他出現(xiàn)在沙皇的后宮時(shí)還有半個(gè)世紀(jì)。
陀斯妥也夫斯基寫他那本小說時(shí)決不會(huì)想到五十年之后會(huì)有那么一個(gè)不可一世的人物。他只不過看到一些在俄國(guó)各地利用地主貴族和無知農(nóng)民的愚昧而行騙的騙子而已;然而,他以一個(gè)大作家所具有的敏感,把這些現(xiàn)象加以抽象概括,然后再賦予具體的形象,寫出了這樣一部有預(yù)言意義的杰作。
亨利希·曼的《順民》(一九一四年)預(yù)示了納粹黨的興起;托馬斯·曼的中篇《馬里奧和魔術(shù)師》(一九二九年)預(yù)示了意大利法西斯的最終滅亡。美國(guó)奧尼爾在二十年代有一個(gè)劇本《瓊斯皇帝》,這出戲里的那個(gè)暴君赫然竟象是阿明和博卡薩之流的前身(順便在此一提,《瓊斯皇帝》對(duì)中國(guó)三十年代的劇作家發(fā)生過影響)。這些作品都可以算是有意或無意的不同程度的“預(yù)言”。當(dāng)然,所謂“預(yù)言”,并不是真正的未卜先知,但也決不是純屬偶然的巧合。所謂“預(yù)言”,乃是推理的一種獨(dú)特方式。一個(gè)真正的詩人和作家,對(duì)現(xiàn)實(shí)觀察和體會(huì)得深刻,對(duì)未來事物的萌芽自然會(huì)產(chǎn)生一種敏感。以這種敏感來創(chuàng)作,所創(chuàng)作的作品就能成為某種程度的預(yù)言。
《洋涇浜奇?zhèn)b》之所以可稱為預(yù)言性小說,就因?yàn)樗x取的主題是在舊中國(guó)社會(huì)里潛藏著還有充分活力的一股反動(dòng)的破壞性封建勢(shì)力。這股破壞力卻又很不受人注意,以為那只是一些江湖騙子,沒有什么了不得。而后來的事實(shí)都證明并非如此,反動(dòng)會(huì)道門及各種反動(dòng)幫會(huì)組織,解放前無惡不作,解放后還蠢蠢欲動(dòng);直到現(xiàn)在是否完全清除干凈,還未可斷言。《洋涇浜奇?zhèn)b》這樣的小說,不能說今天已沒有生命力和現(xiàn)實(shí)意義了。
突然想談?wù)劇堆鬀茕浩鎮(zhèn)b》這部幾乎已被人遺忘的出版物,有一個(gè)直接原因是近來看到一些香港出版物,略知“現(xiàn)代化的”香港目前還有比《江湖奇?zhèn)b傳》更荒唐不經(jīng)的武俠小說,比《火燒紅蓮寺》更低級(jí)的電影,其風(fēng)行情況比二十年代、三十年代在上海還有過之而無不及。
香港的事情不是我想談的,問題是香港近在咫尺,風(fēng)很容易吹來。杞人憂天,便不由得懷念起中國(guó)三十年代的塞萬提斯了。
當(dāng)然象還珠樓主那樣的武俠小說不大會(huì)再在我們的出版界出現(xiàn)了,然而安知不會(huì)有某種不健康的東西以通俗的或不通俗的形式慢慢露頭,甚至風(fēng)行呢?當(dāng)然通俗文學(xué)不容一筆抹殺,這個(gè)方面我們也是討論的不夠的。這個(gè)問題需要專門寫一篇文章來談才行;從《洋涇浜奇?zhèn)b》所產(chǎn)生的感想,說到這里就結(jié)束吧。
一九八一年二月八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