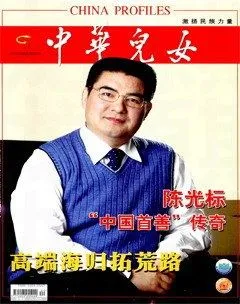劉亮程 一個人的“村莊”
“噠噠”的拖拉機聲敲碎了村莊的夜晚,零星的一兩聲雞鳴單薄地夾雜在機器聲中。一到傍晚,揚起滿天塵土的羊群不見了,路上飛奔的拖拉機一樣可以制造如此效果。牽著老牛回家的場景基本是在回憶的膠片里,五歲以下的孩子需要借助圖畫以及電視認識那個龐大而善良的動物。或許不久的將來,這里的孩子看見一匹馬跑過來,會很大聲地喊“駱駝”——這是幾年前流傳在這個村莊的笑話,用以嘲笑那個從城里來的、沒見過世面的、將馬認成駱駝的小孩。
現在,這里的孩子也逐漸忘卻了活躍在田野里的牲畜,還好,他們還有大片茁壯翠綠的莊稼地,可以捉迷藏翻跟斗,童年不至于太無趣;還好,他們還有劉亮程,他記下了曾經真實存在的村莊,很多事情不至于了無痕跡。
一個人的村莊與一群人的村莊
說起劉亮程,很多人會淡淡一笑:過時了。畢竟,《一個人的村莊》是10年前的事。10年時間,有多少新書出版啊,10個村莊的樹化成紙送進印刷廠都不夠,新華書店制作排行榜的人都換了一茬又一茬了;10年前的小孩現在都快出10本書了,比如蔣方舟。那個只會寫村莊,黑夜,麥田的劉亮程當然是過時了。
但是,許多人還是非常懷念劉亮程筆下的那片鄉村。
劉亮程的鄉村,存在于他的散文集《一個人的村莊》里,也存在于真實的地理版圖中——新疆北部沙漠邊緣那個名叫黃沙梁的村莊,因為有了劉亮程的書寫,開始成為很多人幻想中鄉土的代名詞。劉亮程用詩性的語言,很有耐心地講述著這里一頭牛的眼神,一朵花的笑聲,一場風的痕跡。
如今,這里仍然只有三十幾戶人家,一些老人還記得童年時的劉亮程。這個村里的人仍然不怎么愛看書,不過還是會有幾個好奇的人會翻到書里找人名:韓三,邱老二,馮三……村里人會順著他的書回憶曾經發生的事。而劉亮程童年生活過的房子,因為長久無人居住,已經搖搖欲墜。
“他小名叫劉二吧,小時候不愛說話,老是一個人吆喝著一群羊在河灘里轉悠,誰知道一肚子的話都寫成書了。”村里一個老太太說,“前年,還有電視臺的人來這里拍,什么羊圈、菜園子都拍了一遍,哪里舊往哪里走……他是不是出名了?”
出了名的劉亮程有時也會回來一趟。村里的人見了他會和他淡淡地打聲招呼,然后就各忙各的去了。這個村莊比以前忙了。村莊在改變,劉亮程也在改變――
那個曾經扛著鐵鍬滿村轉,看螞蟻打架,蹲在墻角曬太陽的劉亮程,現在已經是新疆作協副主席。他會經常成為某個講座的座上賓;習慣了在新疆與內地的時差間走來走去;逐漸適應端坐主席臺侃侃而言;喜歡背著電腦寫作;適應了城市的肯德基和可樂……沒有什么好奇怪的,他來城市生活已經17年了。
城市生活與鄉村生活
1993年,劉亮程舉家遷往烏魯木齊,這在農村是一件了不得的大事,意味著范進中舉,鯉魚跳龍門。但是在劉亮程心里,或許1998年才是真正意義上的龍門一躍——《一個人的村莊》出版,在《南方周末》上連載,《天涯》雜志重磅推薦,數位名家力捧,被譽為20世紀最后的文學景觀,摘獲第二屆“馮牧文學獎”……榮譽忽然如同天降暴雨,刷刷地砸落在這個來自西部、寫農村生活的中年男人身上。
在此之前,他是一個八歲喪父的孤獨男孩,是黃沙梁村的一個“閑錘子”,是農機管理站的管理員,寫了多年詩歌,并自己出版詩集——一個標準的文青。因為文學在當地的匱乏,他有點不合時宜也有點與眾不同。沒有什么宏大的文學夢,寫詩只是生活的一部分,很多詩句寫在隨手能看到的紙片上,后來不知所終。
“進入城市后,關于鄉村的回憶涌上來,想寫下來,但是找不到出口。”劉亮程慢慢回憶,“后來,有一次喝酒,酒桌上一個朋友的話讓我有了感覺,這個朋友在外面有很多債討不回來,他一邊喝酒一邊氣呼呼地說,我就不信我要不回來,我一家家地要,那些錢能買多少酒喝啊。”說不上哪里讓他有了感覺,他自此開始動筆寫村莊的事情,一件一件的寫,不緊不慢。
說這些話的劉亮程此刻正行走在北京的大街上,車水馬龍,人群熙攘。但是他嘟噥著表示:“走在北京的大街上和走在鄉村一樣。”這次來北京,他先去魯迅文學院與學員做交流,又到北大學習交流了幾天,“就是和那幫孩子聊著玩兒。”他是指魯院的交流。但那幫孩子并沒有讓他省心,有一個女孩質疑他的農村生活寫得太詩意,沒有現實中的猙獰,并佐以《白鹿原》為證。
“你舉的例子也是來源于文學作品呀。”劉亮程機智地迅速反駁。臺下一片笑聲。
繼續有人站起來說他在城市生活得太久,他說:“我后悔沒有早一點來城市,城市更適合人的身體生活,所以被稱為人類的第二家園,鄉村則適合人的心靈。再者,城市生活并不影響創造,《一個人的村莊》就是在城市中完成的。”帶著一點狡黠的倔強,劉亮程在一次次辯論中略占上風。
但是,當他在城市里呆得久了,累的時候,還會回到黃沙梁,“當他的心一有不安的時候,有關黃沙梁的一切就都成了他的鎮定劑。”這是誰說的呢?劉亮程的黃沙梁,有時如同郝斯佳的塔拉莊園,是站上去就能獲得力量的神奇土地。
他坦誠地認為寫散文是沒有大出息的,雖然他也是以散文成名。不知是不是由于這個原因,他后來創作了《虛土》,一個依然以村莊為載體的小說。但是《虛土》并未獲得《一個人的村莊》那樣的成功,有人說《虛土》是有散文基因的小說怪胎,關于這一點,劉亮程的看法是:“我只是寫出了我心中的鄉村,至于是小說,是長詩還是散文,形式有什么重要的呢?”
他不介意被人稱為西部作家,“我寫作時從來沒有感到我是在西部。西部這個概念本身有點文化歧視的味道。我在你的西邊,你就叫我西部,一副文化中心霸權面目。一個作家不應有這樣的心理限制。”
但他的新作卻再也沒有《一個人的村莊》那樣火爆。
《鑿空》依然是以新疆為背景的長篇小說。大規模工業挖掘下,村莊正在被鑿空。故事的背景被移植在了南疆。
今年7月3日,《鑿空》研討會在北京宋莊盛大舉行,在市場上反應依然寂寂。新疆大開發,各路人馬呼嘯奔向南疆,摩拳擦掌,躍躍欲試,想在這塊還未被充分開墾的土地上掘金。現在,推土機日夜轟鳴,每個人都在鑿,鑿,誰會在意一個作家的《鑿空》?誰會在意村莊的失落?
現實的農村與詩意的鄉村
這個在講臺前能言善辯的劉亮程,私下里以沉默居多,走路喜歡低著頭,腳步輕,且慢。酒桌上喝酒卻頗具俠風,劃拳技術一流,聲音低,快,得勝后有一點小得意,笑時嘴角向上彎,眉眼都開了花。
他有著農民的淳樸也有著農民的狡猾。他承認他知道王朔、韓寒這些文化現象,也知道時下發生的熱門文化事件,卻堅決不予以評價,以防落他人口實。他只會部分敞開自己,而且小心翼翼。粗放只是在酒桌上,除此之外,他是一個沉默的,克制的中年男人。
偶爾他也會頑皮。比如,坐在北大未名湖畔的博雅塔下,接過有人遞來的面包,他會飛快地向上看一眼,憂心忡忡地說:“我們坐在這里吃,烏鴉會不開心的吧,我們吃,它在上面旁觀,是不是不大人道?”
有人贈他“鄉村哲學家”的美譽,他擺擺手:“這是一頂并不適合我戴的破草帽。”討論起作家的天賦問題,他說:“什么天賦,我覺得天賦可能是你小時候挨過的一個磚塊,‘砰’地砸開了你腦袋里的某一個開關而已。”而語言,他認為是養熟的狗,需要的時候自己就跑來。
他慣常說的一句話是:“老子,莊子,屈原,都曾經影響過我。但他們對我的影響,肯定不會有我家鄉的一場風對我的影響更大。”這場風出現在很多場合,因為總是有人問起他深受哪位大師的影響。有意思的是他對莊子的理解――“好像莊子就是我們村里一個姓莊的老頭。他描述的那些風、秋水、山木、死亡……似乎都在我們村里。我能聽懂他說的話。”
選擇莊子做鄰居的劉亮程其實也很入世。他也曾試圖在城市開一個“鄉村酒吧”,但最終以失敗告終。他也被卷入文人圈的口水賬,出版人賀雄飛在網上對他的痛罵傳得沸沸揚揚,有看熱鬧的人希望看到他的反擊檄文。對此,他選擇沉默。
他并非只關注村里的風,大火,漫天黑夜。他也關注現實的寫實文學,“南方有一個打工妹——是鄭小瓊吧,她的文字很打動我。”
《中華兒女》:說一說你眼中的鄉村。
劉亮程:其實鄉村和農村是截然不同的兩個概念。鄉村是詩意的文化的精神的,而農村是現實的;鄉村是從我們古老的詩經、莊子、唐宋詩詞以及山水國畫中營造出來的一處家園,是中國人的伊甸園,而農村是我們現實的生存地。我認為自詩經、莊子、唐宋詩詞以后,鄉村在中國已經消失了。
《中華兒女》:那你對農民又做何理解?
劉亮程:我們理解的農民有兩種:一種農民是話語中的農民,當某個人當討厭某個人的時候,就說他是農民。我們這個社會有一多半人是“農民”,這一部分農民從農村走向城市,但他們永遠走不到城市中心;或者就算他們走到城市中間,來到上層社會,我們也能一眼認出。因為我們太熟悉農民了,知道農民就是什么樣子,我們看到他某個小動作,我們就會認為是農民的動作;大家說某一句話的時候,我們認為這是農民言語,所以說某一個人是“農民”的時候,我覺得已經說到根子上。
還有一種農民,就是此時此刻,還在面朝黃土背朝天辛勤耕作的那一部分農民,他們是農民的大眾。這一部分我們不認識,因為他們從來沒有像前一部分農民一樣,走入城市,走到我們眼前。
《中華兒女》:你如何理解當下作家的職責?
劉亮程:我覺得作家也是人,應該有兩種狀態:第一個狀態就是人的狀態,平常人的狀態。第二個狀態是作家的狀態。當我們是人的狀態的時候,有可能我們是農民,是工人,是官員,是知識分子。但當我們是作家狀態的時候,我們應該是一種完整的、獨立的個體。是人的狀態時,我們是這個世界的一部分;是作家狀態的時候,我們要將自己放在世界的對面,世界是世界,我是我,這是一個作家狀態。
我想起我在鄉下的時候,經常看到鄉下的狗,我認為鄉下的狗具備一個作家的狀態。有過鄉村經驗的人都知道,鄉下的狗是沒有狗食的,狗都是自己找食吃。喂豬的時候,狗搶著吃一口;喂雞的時候,狗搶著吃半嘴;更多的時候,狗溜著墻根找食吃,以我們認為最不屑的骯臟之物果腹,這就是白天的狗。但是,到了夜晚,月亮升起來了,人們睡著的時候,鄉下的狗蹲在草垛上,蹲在房頂上,用舌頭舔凈自己的爪子,梳理好自己的皮毛,然后,脖子朝上,腰朝上,頭對著月亮,汪汪地叫。這時候的狗截然不同于白天的狗。我們好多人只看到白天在墻根找屎吃的狗,我們沒有看到在夜深人靜時對著天空,對著月亮,汪汪高叫的狗。這時候的狗是自由的,它的叫聲沒有任何恩怨,它不再為一口食而叫,它的叫聲像吟誦和祈禱。我覺得作家應該發出這樣的聲音,夜晚狗的聲音。
《中華兒女》:最近,看到你的好幾本書在書架上,出名后寫字的速度快了嗎?
劉亮程:不是。《風中的院門》很多內容是《一個人的村莊》里的,至于你看到的《驢車上的龜茲》等這些新疆游記,是很多年前寫的東西,我寫一個東西,一般準備四五年,寫兩三年,這就八年,跟抗日戰爭一樣